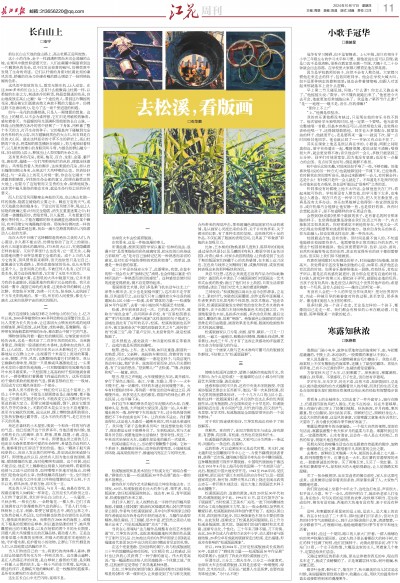□ 黄披星
冠华有学习障碍,但不是智障者。上七年级,却只有相当于小学三年级左右的学习水平和习惯。据他爸说生活可以自理,就是口齿不是很清晰,很难在教室里坐满一节课,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就会出去游荡。在学校里大家都习惯看见他在那晃荡。
因为是学校教师的孩子,自然不会有人欺负他。大家都习惯他走来走去的样子,包括同班同学。他会在学校大喊大叫,但不是那种病态的歇斯底里;他也会带着情绪喊,但跟人对话起来那就基本上没什么逻辑。
早上第二节又碰见他,问他:“什么课?你怎么又跑出来了。”他摇摇头说:“数学。听不懂我就跑出来了。”他爸爸今天去开会,他就更加经常地跑出来了。我逗他:“第四节什么课?”“是……地理……哦不是,音乐,你的课嘛!”
“那你上不上?”
“上。”他倒是很坚决。
我的音乐课他都没有缺过,只是现在他的音乐书找不到了。每次留给学生独唱的时间,他一定第一个要唱。他无法很完整地唱一首歌,但基本音准还可以;虽然烦他太闹,也觉得应该给他唱一下,还得鼓励鼓励他。同学也大多很配合,鼓掌加油的样子,他就很开心,老是要再来一遍——就说下次,留一点时间给其他同学。他也就认同了——开始又有点坐不住了。
其实在课堂上他还是很认真在学的,小眼镜,两眼之间距离很近,眉宇有些蹙在一起,嘴唇很薄,爱说话却不清晰;唱得很大声,就会更觉得不准;音乐他会听一会儿,多数只能坚持三五分钟。同学们对他很宽容,因为他没有恶意;也没有一点暴力的企图。有点好笑也好玩,倒是离群不索居。
初中音乐比较无趣,对他来说似乎难了一些,不够有趣。但他喜欢唱(说的另一种方式)也就能够坚持一节课下来,已经难得。有时候我在房间里听音乐,他会过来跟着听一会儿,有时候会问:这是什么?有时候只是听一会儿就走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听的音乐对他来说有点艰深,但也没听他说过“很难听”之类的话。
听同事说有时候晚上他不太听话,会被他爸关在门外,看起来挺可怜的。学校里没有人欺负他,但学习落下太多,也难免让人着急。现在只有这一种学习方法,把人关在教室里,也真是没有太多办法。音乐如果能够让他得到一些宣泄或是快乐,或许机缘巧合能够让他安静一些,也是很好的事。我有时会想起这孩子,却不知道哪样的音乐更适合他。
会想到《铁皮鼓》里那个敲鼓的孩子,还有著名的阿甘那奔跑的样子。也觉得他就像是游离在我们生活之外的一个,有点抽象其实很具体的。你经常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可他又会一次次出现在你需要帮衬或者照看的地方。他有自身快乐的体系,你无法融入;却也觉得这样也好,像一种浅生活。
校园最适合他,没有伤害。但时间是最不饶人的,不知道他能够在校园里待多久。他需要很多正常功课以外的东西,可惜这个校园很难提供。他应该更需要声音、色彩、运动、游戏、自然和采摘等等这类的东西,甚至我觉得所有的孩子都很需要这些,但实际上我们却不能做到。
我喜欢他唱歌时无所顾忌的样子,时而偏离时而准确,但很高兴。我觉得音乐还没有触动到他的心弦,如果有,或许他还会有沉思的时刻。如果音乐能够陪他走一段路,有些快乐,有些忘乎所以,要是还有些感伤就更好,因为那会是更有启迪的时刻。《13骇人游戏》中的第三关:要把孩子弄哭,就要抢走他的玩具。当孩子没有玩具时,他是没空认真听这个世界其他声音的;希望他有一个玩具,没有人会抢它——像自己的听觉一样。
有没有人会把一个人的听觉当作玩具呢?把对世界的听觉,当成一种被引导的被善意对待的过程,甚至享受,那多美好。像电影《美丽人生》里的那样。
很多时候,陪一个孩子走走,无论是怎样的一个孩子,都像陪自己走走一样。我们都会有相似的心率在跳动着,只是跳着,简单得像某一首歌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