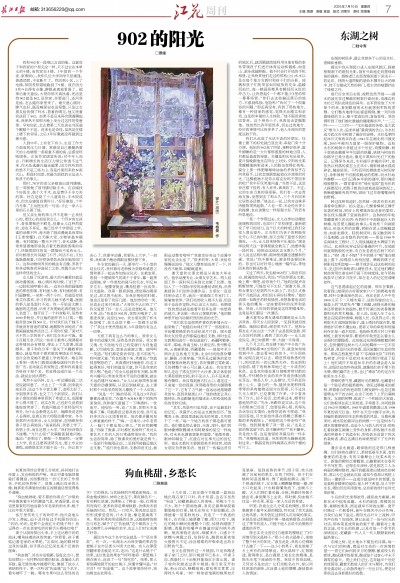□ 陈前进
初夏的雨丝总带着几分顽皮,斜斜地打在纱窗上,发出细碎的声响。我正对着电脑屏幕敲打着键盘,试图整理出一份冗长的工作报告,手机却突然响了。屏幕上跳出母亲的头像,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在视频通话里显得格外清晰。
“狗血桃熟啦,要不要给你寄点?”沙哑的声音裹挟着乡村的潮湿气息,穿透屏幕,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地说着今年老家的雨水多,桃子比往年更大更甜。
客厅里传来儿子的欢呼声,他兴奋地从沙发上弹起,迫不及待抢过手机跟奶奶说:“奶奶,奶奶,是那个会流红汁的桃子吗?我记得有一次在老家吃的时候舌头都染红啦!”
妻子从厨房探出头来,手上还沾着牛奶的泡沫,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你看看,孩子都惦记着老家的水果呢。”言语间,她的眼神穿过我的肩膀,似乎落在记忆深处某个泛黄的画面。
“狗血桃”,其名实是粗鄙,每每念出口,便如同冒出一句村野间的俚俗脏话,直撞进人的耳鼓,毫无修饰地冲撞着听觉,像极了故乡人爽朗的性子。第一次听说“狗血桃”这个名字,着实被吓了一跳。哪有水果叫这么奇怪的名字?它的得名,与其独特的外观紧密相连。当狗血桃成熟时,神奇之处在于,果皮颜色不一,有些鲜红欲滴,仿佛染上了鲜血一般,红得浓烈而绚烂,更多的却是翠绿映眼,仿佛尚未到采摘的时间。然而,一口咬开,果肉却总是红彤彤或紫莹莹的,汁水丰盈,像是要滴落下来。果皮和果肉形成强烈反差,这般独特的颜色与形态,赋予了它“狗血桃”这个颇具乡土气息又略带几分神秘的名字,也让人们对它充满了好奇。
据说当年这个名字完全就是一个“语言事故”。有一次,一伙湖北大冶保安镇的果农担着桃子在市区街头叫卖大红桃。有人在箩筐里翻来看去就是不买,还问:“这是什么桃子?”结果,这位性急的果农气呼呼地将一箩筐桃子倒在街头,还说了一句“狗吃的”。结果,那人看到满地裂开的血红桃子,似懂非懂叫道:“对对对!叫‘狗血桃’”。这个故事很快传开,狗血桃也由此得名。
十几年前,二姑在端午节提着一篮狗血桃出现在家门口时,我才知道,这名字虽然“狗血”,却藏着最动人的美味。那桃子个头不大,却个个圆润饱满,表皮泛着翠绿混着胭脂般的红晕,绒毛在阳光下轻轻颤动,仿佛披着一层柔软的纱。我选了一个熟透的桃子,在衣服上随便擦了擦,便大口咬下,嫣红的桃汁瞬间弥漫整个口腔,惊得我瞪圆了眼睛,清脆的咀嚼声在静谧的屋内格外清晰。桃肉萦绕在齿间,细腻多汁,口感介于软糯与爽脆之间,恰到好处,酸甜如夏夜萤火般明灭不定,丝丝缕缕的纤维牵连出故乡田野的气息。
岳父也曾拥有过一片桃园,只是我踏进妻子家门之时,那片桃园早已易主。听妻子说,鼎盛时三十亩桃林能染红半面山坡。妻子曾向我描述过那片桃园:春日里花开如海,粉云浮动,蜂蝶喧闹;夏初果实累累,压得枝头弯垂,一树一树浓密饱满的桃果如灯笼悬垂。每到成熟的季节,园子里,枝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树枝。孩子们在桃树间追逐嬉戏,馋了就踮起脚尖,摘下一个熟透的桃子,在衣服上蹭蹭随便擦一擦,便大口吃起来,汁水顺着嘴角流下,也顾不上擦。大人们则忙着采摘、分拣,将最好的桃子挑出来,拿到集市上去卖。那时候,狗血桃不仅是一种水果,更是一家人生活的希望。
听罢,我竟生出几分莫名的惆怅:那片承载着妻子童年光景的桃园,终究成了我无法抵达的风景。我未曾见过那枝头沉甸甸的果实,未曾品尝过那桃园中第一缕成熟甜香;如同错过了季节的旅人,只能于他人言语中拾掇些许遗落的芬芳。
陈忠实先生曾在《白鹿原的樱桃红了》中深情写到火晶柿子:“那小小的火晶柿子,浓缩了整个秋天的阳光。”读至此处,我的心仿佛被什么撞了一下——这小小的果子,竟也浓缩了乡土所有的深情厚谊。那火晶柿子,红得剔透,甜得绵长,是白鹿原土地长出的精魂,是陈先生笔下流淌的乡愁。我故乡的狗血桃,又何尝不是如此?它们虽粗名在外,却以同样深浓的滋味,沉淀着土地的馈赠,凝结着亲人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