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学文
经常参加各种活动,涉不同的地方,赏不同的景致。有名山古刹,有乡村野趣,均各具风情。有的地方一次就够了,而有些地方几次都不够,每次都有不同的惊喜。这些地方如经典名著,值得反复翻阅,譬如庐山。
人生中第一次远足即是到庐山。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杂志社在庐山举办笔会,我有幸在受邀之列。从北京到南昌,要坐两天一夜火车,现在想来,太过漫长,但彼时心怀激荡,也为睹庐山真容,虽然颠簸,却未觉疲累。邻座是从京返赣的一家三口,老者外向,一路向我讲述他熟知的江西,从历史传说到市井生活,从风俗习惯到特产美食,可以说给我上了一堂个性化的赣地课。我至今记得他的腔调及那只北京烤鸭。正值夏日,天气炎热。烤鸭吊挂在半开的车窗口,随着火车行进的节拍,飘散着阵阵香味。火车穿越隧道时,塑料袋哗啦啦地响,与火车的呼啸混在一起,如同高音合奏。此刻老者便停止讲述,车出隧道又开始继续,直至夜晚。一家人轮着在座位上睡觉,还让我在他的座位歇息。座位下面多有铺着报纸睡觉的乘客,我展不开身,也就接纳了老者的好意。老者不只让我对赣地有了初步了解,也吊足了我的胃口。因而,乘坐中巴由山脚到牯岭镇盘旋而上,近一小时的车程,我的目光往各个方向游走,没有感觉丝毫单调沉闷。这符合我对庐山的想象。一步登顶,还叫什么名山?文学议题结束,集体出游,观五老峰,望三叠泉瀑布。山是登上去了,但没看到五老峰的相貌。那日云遮雾罩,能见度不足三米,只能凭着李白的诗句“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在脑里描画了。有些遗憾,但云雾翻卷本就是庐山胜景,连庐山产的茶也名云雾茶,轻易识得真容,就不是庐山了。三叠泉瀑布也未见,一文友崴了脚,我和另一文友扶携着断后,没赶上大部队,走错了方向。
第二次去庐山也因文学邀约,细雨淅沥,计划去的地方不能去了,当然没歇着,庐山有险峰,也有幽谷,有清泉,也有秘洞,处处皆风景。
此次又往,仍为叙话文学。白露临近,秋意渐浓。再不是如以往那样盘旋而上,而是乘坐索道缆车。如遇暴雨,缆车就停了。那晚是晴日,乘的是我见过的最大缆车,可容纳十余人。缆车上行,暮色已深,一轮明月挂在东天,又像悬浮在树梢,大而圆,轻而薄,缆车奔着月亮去,月亮似乎也在向缆车靠拢。我在草原大漠均见过圆月,凌空还是第一次。月亮似乎更近了,随时可拥抱入怀。回望,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九江市璀璨的灯火高高低低,如一簇簇绽放的菊花,生机盎然,流光溢彩。
庐山的天多变,“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夜晚视线通透,也许白日云雾就流散了。氧气充足,睡眠香甜,醒来已7点多了,拉开窗帘,睹见蓝天白云,心中大喜,还没看过艳阳下的庐山容颜,此行或可遂愿。
庐山自然景观很多,除了三叠泉瀑布、五老峰,还有含鄱口、芦林湖、锦绣谷等,那日去的是锦绣谷。清早的空气湿漉漉的,也许深夜落过雨,或许庐山的秋天就是如此,雾消露结,似有蒸汽拂过,身心都舒展许多。日头渐高,温度徐升,湛蓝的天空中数朵闲云游弋,如野鹤翩跹。
庐山的核心区域牯岭镇没有笔直平坦的路,多半的路都有牛角的弧度,藤蔓般缠绕绾结,近似迷宫。作家王祥夫曾讲傍晚逛牯岭街的经历,看到路中央横着半截树枝,正要去捡拾,树枝忽然动了,瞬间消失不见,原来是蛇。庐山生态好,这也是例证吧。我数次于牯岭街道盘桓,王祥夫的故事并未令我生惧,只是多了些许小心。
核心区之外的路就更不可能平坦了,上石阶下石阶,几个回合,背腹尽湿。当然体验也是绝妙的,四周皆石,石上生木,高矮错落,姿态万千。自然是最好的神工,无需任何雕饰。
传说中的天桥并不是横跨峡谷的石桥,而是状如牛舌、悬在岸边的巨石。对面山石笔直,如同斧削。天空的云团已呈川状,如被撕扯而又绵延的棉絮。从峡谷望过去,便能看到九江市一隅。
庐山的真容就该如此吧,终于偿愿。待下行上攀,至仙人洞,思绪旋又翻转。云雾缭绕的庐山,骄阳映照的庐山,细雨霏霏的庐山,都是庐山的一面。庐山的基本相貌会随阴晴雨雪变幻,而就个体的认识,庐山更是永远变动不居。这就归属文学范畴了,山之所以名,水之所以灵,自然景观只是其一,文学滋养才得永恒传播。
庐山一向与文学有缘,当然也可反过来讲,诗家向来钟情庐山,比如陶渊明,比如李白,比如白居易,比如苏轼。
陶渊明即九江市(浔阳柴桑)人,29岁第一次外出,任江州祭酒。因为“不堪吏职”,没多久便辞职回乡。陶渊明的仕途是断断续续的,几度出几度归,41岁辞去彭泽县令,决意归隐田园,写下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陶渊明的大半时光是在故乡度过的,他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应是庐山。据说,陶渊明死后就葬于庐山脚下,惜年代久远,墓园已难觅踪迹。他笔下的桃花源虽是虚构的,但灵感应源于庐山。隐于野,而精神始终在远行。桃花源亦成为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家园。
李白一生多次登临庐山。25岁,李白出蜀远游,写下两首《望庐山瀑布》:其一“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气势如虹,亦可见李白“上穷碧落下黄泉”之诗风。“安史之乱”后,李白再登庐山,写下了《望庐山五老峰》,此时的庐山是李白心目中的桃花源,是避世的绝佳场所。如果不是东巡的永王多次邀请,李白或许会在庐山终老。
白居易与庐山的关系亦是佳话。白居易43岁被贬为江州司马,成为闲职,这是他最黯淡的时光,同时亦是他创作的高峰时期。被贬职的第二年,白居易在庐山北香炉峰下,亲手建了三间草堂,并写下《庐山草堂记》。“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另一名篇《琵琶行》写于浔阳江边,亦为千古绝唱。九江市重要的文化景点琵琶亭立于长江岸侧,自为纪念白居易。白居易,琵琶亭,无疑是九江及庐山的重要符号。
两百多年后,48岁的苏轼去汝州任职途中,绕道江西探望弟弟苏辙,并登临庐山,在西林寺墙壁写下七绝《题西林壁》,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背诵:“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唐诗抒情,宋诗说理。《题西林壁》可谓宋诗代表作。
因此,游庐山不仅是赏景,亦是读诗。国人重史,历史、文学史……品味和庐山有关的诗作,也是对文学史的部分复读。
隔日去游庐山西海,其又名柘林湖,面积颇阔,水间藏着8000多座岛屿,故又名万岛湖。岛形状大小各异,皆郁郁葱葱,多生乌桕树、红豆杉、泡桐等。水中有游鱼,天空有飞鸟,举目四望,心神皆清爽。
先前不知,庐山还包蕴着这样一面湖,也许这就是庐山的魅力。
下次再来,定然还有新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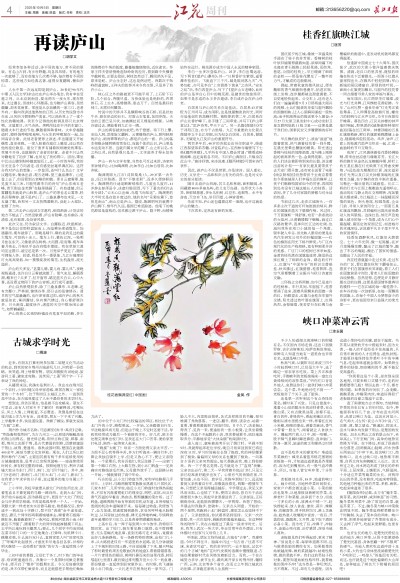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