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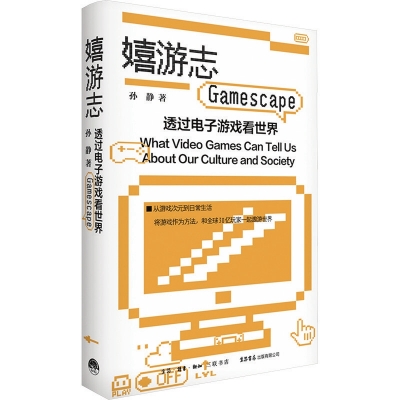
《嬉游志:透过电子游戏看世界》
孙静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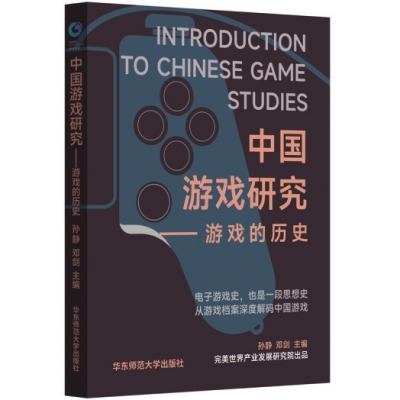
《中国游戏研究:游戏的历史》
孙静 邓剑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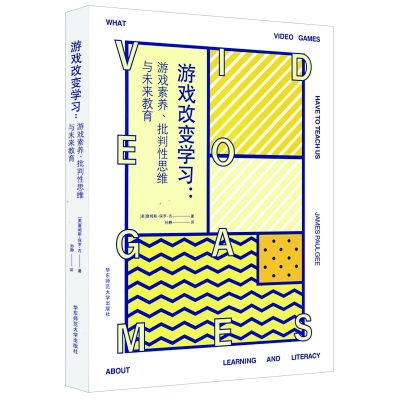
《游戏改变学习:游戏素养、批判性思维与未来教育》
[美] 詹姆斯·保罗·吉 著 孙静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 电子游戏是理解世界的知识之门
在进入所有商店前,妈妈会跟你说什么?A.什么都不要碰 B.什么都不要问 C.什么都不要看 D.以上都正确(正确答案是D)
这是什么?这是美国一款最受欢迎的非裔游戏《吊销黑卡》,2015年出品。它围绕非裔社群的生活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玩家答对的问题越多,说明自己对非裔文化越了解,同时也揭示出自己曾体验过大量隐性或明显的歧视。
如果不是孙静的《嬉游志》,很多人不会知道游戏已经发展到这一步,还有这样的功效。
书里还介绍了《失踪》,这是印度出品的一款融合冒险和解谜的角色扮演游戏,玩家扮演一个被拐卖到红灯区的印度女孩,需要设法逃离,回到家人的身边。
孙静在书中写道:“《失踪》是一款严肃游戏,因为它的首要目的不是娱乐、享受或趣味性,而是想要充分利用游戏的教育功能,讨论人口贩卖这个全球普遍的现实问题,在印度,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印度有9800万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其中有98%是女性,51%是未成年人,而且印度被贩卖的人口至今在以25%的比例递增。”
除了这些沉重、严峻的主题,游戏在全球也发展出了各种风格和流派。有的追求对历史文化的高度还原,比如《刺客信条》系列,就连巴黎圣母院的火灾修复工程,都要参考《刺客信条:大革命》;有的追求心灵治愈和疗伤,比如华人设计师开创的“禅派游戏”,“游戏里没有枪声、爆炸和血”。引导玩家内省,感受生命中的和平与爱。
相形之下,孙静在《嬉游志》中不无遗憾地写道:“中国游戏轻叙事、重对战”。这类游戏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利润相对更高,国内团队已经有了多年的制作经验。开发者无需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去创作复杂的游戏叙事,只需参考成熟的游戏机制,就能完成一款对战游戏,而且游戏代码等游戏素材还可以复用到后续的其他作品中。更为重要的是,此类游戏虽然免费,但游戏内购系统却非常成熟,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吸引玩家付费。“从短期来看,这种模式的确能够快速吸引玩家,刺激国产游戏市场的增长。但从长期来看,这有可能会让国内游戏开发商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探索更具吸引力的游戏叙事和更具创新性的游戏机制,最终导致国产游戏产品由于过度同质化,从而在全球市场中缺乏足够的竞争力。”
电子游戏发展到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供人娱乐的媒介,更是通向理解世界的知识之门。《嬉游志》将50余年的电子游戏史纳入视野,通过对不同历史语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电子游戏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将读者带入更广阔的游戏世界,探寻其中奥义,深度解读1960—2020年的全球热门电子游戏,透过数字的纷繁,为读者提供理解游戏文化内涵、提升游戏素养的路径,进而以电子游戏为媒,理解这个多元复杂的世界。
■ 从2022年回溯到1967年“逆序写作”
《嬉游志》的一大特点是“逆序写作”,全书开篇是2022年中国的一款独立游戏,然后逐步回溯,直至1967年,那是电子游戏萌芽的年代。
孙静告诉长江日报记者,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游戏的技术和文化语境变化太快,即便是现在经常玩游戏的读者,也不一定了解十几年前的游戏。她在大学做讲座的时候,经常会提起1995年的《仙剑奇侠传》,可是很多听众已经不太熟悉这款里程碑式的中国游戏。于是,她决定从年代更近的游戏作品开始,读者更熟悉这些作品,更容易产生共鸣,从而接受这本书的核心视角,“透过游戏看世界”。
“更重要的是,我想尝试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读者建立一个异质性的时间概念,一个‘游戏次元’。它不是一个单向度的线性时间轴,而是一个无边界的跨媒介场域。通过这些时间标记,它连接了世界各地游戏的生产和消费,用游戏链接着不同年代的文学、漫画、电影、电视剧、直播等多种媒介,让我们持续地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来回跳转。借用书里的一句话,这个游戏次元不是一个树状结构,而是一个块茎结构,通过游戏让原本匿名的社会文化元素显现出来,呈现出一种游牧状态。从这个角度上看,这本书本身也是一个以探索为导向的游戏,帮助大家深度理解游戏,理解自身,理解这个世界。”
【访谈】
又是一年暑假,家长和孩子彼此奔忙,补课之余,有没有想过玩一局游戏呢?在游戏学者孙静看来,游戏素养正在成为当下及未来社会的基本技能。如果缺乏足够的游戏素养,很有可能无法理解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个人和社会,甚至看不懂小说和电影。
孙静是西交利物浦大学文化科技学院副教授,最近出版了新书《嬉游志:透过电子游戏看世界》,之前她已出版译著《游戏改变学习:游戏素养、批判性思维与未来教育》《玩家心理学:神经科学、用户体验与游戏设计》,合作编著《全球电竞文化导论》《中国游戏研究:游戏的历史》等。
上周,长江日报《读+》周刊记者专访了孙静。
■ 表层的快感和爽感只是短暂幻象
读+:根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发布的《2021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中国游戏用户已经达到6.6亿人。除了快感、爽感、卖装备,以及少数人成为电竞选手之外,如何让中国青少年玩家在游戏中获得真正的收益?
孙静:这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讨论。像很多游戏从业者和游戏学者一样,我觉得快感、爽感、卖装备、成为职业玩家都不能让青少年从游戏中真正获益。即便是对成年人来说,表层的快感和爽感只是短暂的幻象。至于卖装备和做电竞选手,这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游戏活动了,而是一种工作,对生理和心理条件都有很高的要求。根据相关数据,电竞选手的黄金时期一般是在15至16岁,平均退役年龄为24岁,75%的职业玩家患有腰椎、颈椎、手腕等疾病,能够获得冠军荣誉的人更是少数。由于他们通常会把很多时间投入到日常训练中,错过高中和大学教育,退役后的职业转型也是个严峻的考验。
然而实际上,游戏并不仅仅意味着娱乐和电竞,而是像文学、漫画、电影、音乐一样,是一种媒介。对中国青少年玩家来说,如果想要从游戏中获得真正的收益,关键是要具有“作者思维”。换句话说,不要单向度地接受游戏公司和游戏作品传达给玩家的内容,而是要从游戏制作者的视角出发,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深度理解游戏,还可以尝试用游戏这种媒介来进行自我表达,自己制作游戏。如此一来,游戏才能为青少年带来长期的收益。
读+:当下,我们的困境是什么?
孙静:中国游戏产业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于,游戏自主创新不足,游戏类型过于同质化,产品过于单一。当前的游戏依然以娱乐游戏为主,鲜少涉及游戏的其他应用场景。近年来,虽然严肃游戏已经成为产业关注的热点,但这一游戏类型依然停留在概念阶段,成熟的精品游戏还很欠缺。由于开发经验不足,且本土开发者尚未找到功能游戏的盈利模式,国内的严肃游戏发展明显落后。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游戏企业依然处在自发探索的状态下,过于依赖直接经验,学术研究和产业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国内对电子游戏的学术研究极为欠缺,尤其缺乏高水平的学术专著,缺少针对中国游戏文化的深度阐释。
就游戏研究来说,也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首先,主流游戏话语往往还停留在过度游戏层面,没有跳出“过瘾”与“戒瘾”的限制,尤其缺乏对具体游戏作品的深入分析,缺少批判性思维。
此外,国内学者缺乏讨论游戏的学术平台,如学术会议、学术期刊等。近年来,欧美、大洋洲等地区每年都会举办多次游戏研究的国际会议,如全球电子游戏研究协会的历届年会,其研究对象涉及少量中国游戏文化,但由于语言壁垒,国内参与者较少。虽然协会下设中国区域分会,但令人遗憾的是,会议依然以国外学者为主导,参会语言多为英文,尚未与中国本土学者形成良性的互动。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西方学者不懂汉语,且解读方式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偏见性预设,很容易将中国的游戏文化视作“他者”;另一方面,语言障碍依然将大部分本土学者排除在外,无法实现有效的学术交流。因此,推动兼具国际视野和地域关照的游戏研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此,虽然中国游戏产业一片蓬勃,但实际上却缺乏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想要推动中国游戏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我们需要从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提升公众的游戏素养,以提升游戏品质和欣赏趣味;需要在国内外学者间搭建桥梁,消除双方研究中的断裂;需要沉下心来,严肃地对待游戏研究,推出更多优质的原创成果;需要打通产业和学界,助力游戏产业创新。如此一来,我们才能打破游戏生产方面的垄断,打破我们在国际游戏研究领域的失语状态,提升全球游戏文化的多样性。
■ 精品稀缺,呼唤优质的独立游戏
读+:中国游戏业有没有走出时间消费、金钱消费的路径?
孙静:当前,我们看到的主流国产游戏还是以消费为导向。首先,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早期中国网络游戏的游戏机制。本世纪初,国产游戏以大型网络游戏为主,通常采用“游戏免费,道具收费”的模式,为玩家提供一个无尽的虚拟世界。此间,游戏体验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玩家充值的多少,因此被吐槽是“付费才能赢”。大部分作品不仅缺乏创意,还在尽最大努力鼓励玩家进行时间和金钱上的消费,导致各个年龄层都出现了不少有关过度游戏和非理性消费的社会争议,例如青少年。后来,随着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网络游戏从电脑移植到了移动设备,大部分游戏依然以“游戏免费,增值服务收费”的模式为主。如果说之前的玩家付费是为了在游戏中获得竞争优势,那么现在的玩家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炫耀而付费,例如购买皮肤、抽卡、解锁新功能等等,这是当代社会中的“展示焦虑”。
当然,有人也许会说,自己玩游戏很少或根本不充值。但实际上,这是时间上的消费。就像我在《嬉游志》中指出的那样,玩家似乎觉得自己只是在休闲,但实际上却是被悄然异化为数字劳工,在虚拟世界中做着免费劳动,帮助游戏公司维持着同时在线人数。要知道,对任何一款网络游戏而言,玩家人数的多少,也决定着这款游戏的人气和吸引力,进一步决定着游戏公司的利润。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有钱的在捧钱场,没钱的在捧人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中国游戏产业的核心问题在于,玩家人数和市场收入长期快速增长,但更有创意的、更多样化的游戏精品却极为稀缺。但我认为,独立游戏能够为当前中国游戏生态提供活力。
以冒险解谜游戏《文字游戏》为例,它完全舍弃了国产网络游戏的炫酷视听语言和宏大技术体系,用文字取代了传统的图像式美术设计。游戏以黑白为主色调,游戏的场景和玩家角色都是由中国汉字组合而成的图形,在抽象与具象间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此外,汉字的变化构成了主要的游戏机制。想要解开谜题或取得对战胜利,玩家无须与敌人肉搏,而是要用手中的剑砍去关键汉字的一部分,或是推动不同汉字进行组合。如此一来,汉字成为贯穿这款游戏名词及动词维度的核心——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玩家都感慨“汉字文化博大精深”——无须借助任何外部活动,便能达成玩家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认同。在此过程中,作为文化遗产的汉字和作为新媒介的电子游戏实现了双向赋能。
读+:全书以中国的独立游戏《文字游戏》开篇,这是否表达了您对中国独立游戏、严肃游戏的某种愿景?
孙静:在我看来,独立游戏是整个游戏图景的一个灯塔,人们会把它和商业大作对应。后者通常是由科技大厂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用工业流水线的方式制作出来,主要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在开发过程中,游戏公司往往会锚定当下火爆的游戏,用类似的甚至一模一样的游戏机制来生产同质化的游戏,因此出现了很多“换皮游戏”。
在《嬉游志》中,我把《文字游戏》标记为中国独立游戏的新浪潮,就是因为它通过交互叙事把游戏这种新媒介与汉字这种传统文化深度融合起来,不仅打破了传统商业游戏的套路,而且还在独立游戏这个赛道上实现了创新。《文字游戏》让玩家通过重组汉字来完成解谜,是一款可圈可点的游戏佳作。
独立游戏的内核强调批判思维,可能是资金层面,可能是文化层面,可能是美学层面,还可能兼而有之。只有对之前的游戏创作惯例进行反思和突破,才会出现独立游戏佳作。从某种程度上说,严肃游戏也是如此。我认为,严肃游戏从本质上看都是教育游戏,这类产品打破了纯粹娱乐的限制,将游戏拓展到更多的应用场景,兼具功能性和趣味性,让游戏本身承载了更大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可以说,独立游戏和严肃游戏都在持续拓展着游戏这一互动媒介的边界,寻求更多可能性和多样性,与游戏消费者的深度需求契合,未来可期。作为玩家和游戏学者,我也希望未来能够体验到更多更具创新性的独立游戏和严肃游戏作品。
■ 批判思维是游戏素养的内核
读+:您的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游戏素养”,这是为了更好地玩游戏吗?游戏素养对人生有什么好处呢?
孙静:游戏素养的概念,来自语言学家、游戏学者詹姆斯·保罗·吉教授。他认为,游戏就是一种涵盖多模态符号的互动语言系统,游戏素养也包括输入技能和输出技能,前者指分析理解游戏的能力,后者则指制作游戏的能力。其中,批判思维是游戏素养的内核,不仅能让我们反思游戏本身,而且还能用游戏来反思日常生活。
提升游戏素养是没办法让我们成为游戏高手的!打游戏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反复甚至枯燥的反复训练,就像电竞选手那样。然而,游戏素养可以帮助我们透过游戏看世界。
电子游戏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游戏思维也是人们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近年来,“游戏感”成为大众文化的新趋势和重要元素,比如《达·芬奇密码》《雪国列车》,都渗透了浓重的游戏感,很多国产影视、小说也吸收了大量游戏元素。可以说,游戏思维早已突破了亚文化的范畴,融入了大家的日常生活,游戏素养是当下及未来社会的基本技能。如果缺乏足够的游戏素养,很有可能无法理解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个人和社会,甚至看不懂小说和电影。举例来说,今年高考的作文题与人工智能有关,如果考生从未接触过人工智能,怎么能写好这篇作文?
随着游戏素养的提升,我们作为游戏的受众,将能够理解游戏不仅仅是屏幕前的小世界,而是我们所处的大世界的隐喻。分析解码游戏的过程,就是我们深度认知社会文化的过程。如果有些人愿意制作游戏,成为了游戏的作者,游戏素养的提升进一步意味着掌握创作游戏的技能,通过游戏设计和游戏开发来传达自身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并进一步影响更大的人群。
更重要的是,游戏素养的提升,不仅能惠及个人,还能让整个游戏生态受益。之前我们讨论过中国游戏产业面临的诸多问题,例如游戏产品同质化、以消费为导向、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游戏精品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内缺乏成熟的游戏教育和游戏研究体系,导致游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过于依赖直接经验,缺乏对游戏的深度理解。只有全面提升游戏开发者、玩家、政策制定者、媒体的游戏素养,我们才能在游戏生态中建构一个良性循环。《嬉游志》就是这样一个尝试,帮助大家理解游戏素养,获取分析游戏的方法,是提升游戏素养的一个工具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