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4年,李政道(左一)与叶铭汉讨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方案中的问题。
图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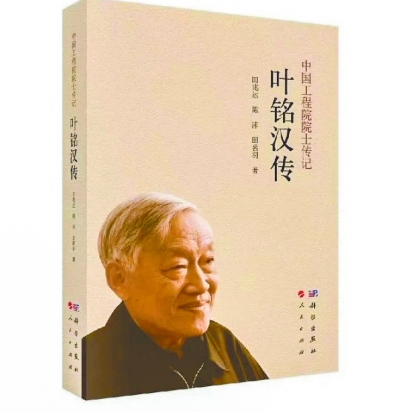
《叶铭汉传》
田兆运 陈沫 田茗羽 著
科学出版社
【编者按】
加速器是了解宇宙奥秘、观察微观粒子世界最重要的大科学装置之一。1988年,中国建成了第一个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这个过程充满波折。叶铭汉是对撞机工程的主要科技领导之一,《叶铭汉传》披露,如果1980年不果断转向,真的花费7亿元建造500亿电子伏的质子加速器,建成后将很难进行前沿的物理研究,而且运行费用将很高——按照国际经验,质子加速器每年的运行费用大约是建造投资的10%,其结果就是中国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大挫折。
书中还披露,李政道先生在这一“转向”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报在此摘编书中相关内容。
李政道先生于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8月4日在旧金山逝世,享年98岁。
■ 20年间,中国高能加速器历经风雨
1953年,美国建成一台高能质子同步加速器,能量为33亿电子伏,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物理学家赵忠尧、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肖健等对这台加速器十分留意,大家分工做了调研,专门开了一次面向全所的学术报告会。
1956年,我国政府决定开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当时,我国参加了位于苏联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每年缴纳运行费约1000万美元。在当时国家财政总收入较低的情况下,这一笔钱是相当可观的。
20年间,我国高能加速器6次上马,6次下马。
1977年,第7次上马。计划到1987年底,建成一台4000亿电子伏左右的质子同步加速器,20世纪末建成世界第一流的高能加速器,做出世界第一流的成果。工程代号“八七工程”。
这一决定是非常先进且振奋人心的,叶铭汉当时也十分激动。但现在看来,这一决定却有冒进之失。只看到高能物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具体条件。首先,国家的当务之急是什么?以我国当时的工业和科研水平,我们有足够的人力来完成这一计划吗?假定国家拨付足够的研究经费,我们能按计划完成吗?
当时叶铭汉等科研人员非常乐观,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高能物理并没有“两弹一星”那样高级别的优先权,因此目标设定得过于激进。
1977年2月李政道到中国访问时,中国科学院告诉他中国已经有了建造高能质子加速器的初步方案,并开始了预制研究工程。12月,他和吴健雄、袁家骝知道了“八七工程”的内容,三人都不赞同这个质子加速器方案。他们一向尊重中国政府的决定,但是这次,他们觉得有些意见还是应该反映给高能物理研究所参考,因此三人联名给时任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写了一封信。
他们所表达的是:首先是尊重中国政府做出的决定;如果要问他们的建议,他们倾向于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他们在信中还详细阐述了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优点,罗列了可以做的前沿物理研究项目,以及同步辐射的应用。事实上,后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后,最初做的几个实验都在他们的信中有所提及。
但是这封信并没有在所里广泛传阅。
■ “八七工程”下马,高能物理发展不断线
1980年,“八七工程”下马,这是第7次下马。虽然工程下马,但国家已经拨给了高能物理研究所一笔预制经费,下马时,还有余款9000万元没有使用。
李政道在1980年底得知“八七工程”下马的消息,感到十分突然。但他又庆幸,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全取消高能物理的发展计划,而是指示“高能物理发展不断线”,并要求中国科学院尽快提出调整方案。李政道十分担心,如果不能及时确定合适的调整方案,中国的高能物理发展又会错过时机,多年的努力将化为流水。因此,李政道决心力挽狂澜于既倒。
1980年12月中,李政道到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参加一个会议,他特地组织讨论了中国高能加速器问题。充分讨论后大家认识到,9000万元人民币足以建造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而且其亮度有望超过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对撞机的亮度。李政道还认为,高能物理合作是中美两国签署过协议且正在执行中的合作项目,应该继续保持。
按计划,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将于1981年6月在北京召开。李政道急忙打电话给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议派人到美国介绍调整后的方案,邀请美国的高能物理专家来华参加讨论。
李政道还以私人名义出面邀请美国五大高能物理实验室的专家到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开会,并邀请中国派人参加,共同探讨在质子同步加速器下马后,中国在新形势下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高能加速器。
中国派朱洪元、谢家麟、叶铭汉参加,大家讨论后,与会大多数学者同意,向中国政府建议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
■ 曲折反复,正负电子对撞机横空出世
结束在美国的访问后,朱洪元和谢家麟返回国内,将对撞机方案汇报给领导和有关方面,解释疑问,争取支持。但是此时国内赞成建造质子加速器的仍然大有人在,朱洪元、谢家麟做了大量工作,打消了很多人的顾虑。
1981年5月初,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与“八七工程”项目组联合召开了香山科学会议,国内很多知名物理学家参加。经过多次汇报、论证与讨论,国内舆论逐渐转向有利于对撞机的方向。1981年7月,高能物理研究所内成立了对撞机筹备组,希望把全所的工作重心转到对撞机的方向上来。这样,对撞机的研制进程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看似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已是板上钉钉了,可谁能想到,就在这时,差一点又回到建造质子加速器的老路。1981年9月,朱洪元、谢家麟和中国科学院二局副局长邓照明三位到美国,为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做准备。出发前,他们接到指示要他们仍然坚持建造质子加速器的方案。到美国后,他们三人向李政道传达了这一指示。李政道十分诧异:这样举棋不定,反复变化,对电子还是质子这个大方向仍不确定,那么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应该怎么开?
李政道以海外学者对我国高能物理事业的一片赤诚,极力做说服推动工作。邓照明与国内通了电话,经过有关领导再次郑重研究,终于肯定了正负电子对撞机这个大方向。
1981年10月15日,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在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召开了非正式会议,中方正式通报了中国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决定。年底,邓小平接见李政道时,李政道向他报告了对撞机的建设情况,邓小平表示这项工程已经定了要干,不再犹豫不决了,应在五年或稍短的时间里建成,经费可以放宽一点,要配备较强的领导班子。从此,中国对撞机的建设真正走上了轨道。这是第8次上马。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后,实际开销和预算十分接近,还略有结余。
现在叶铭汉回顾我国高能物理发展的“七下八上”经历时,感慨1980年初“八七工程”被迫下马,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次下马,虽然一时间内让国内外高能物理学者灰心丧气,但客观上促使大家重新考虑,放弃了建造质子加速器方案,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在这个曲折的过程中,李政道以炎黄子孙的赤诚,一心以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为己任,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他经常回国或通过电话长时间地与国内联系,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他坚持正确的方向,耐心做工作,为我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