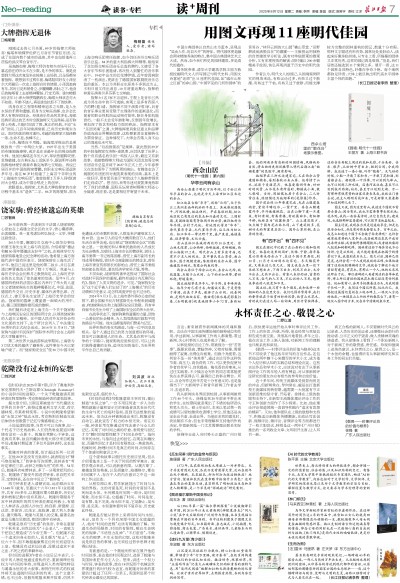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 刘洪波
《读书》杂志2025年第7期,评介了奥地利作家克里斯托夫·兰斯迈耶(Christoph Ransmayr)的小说《时间的进程》,一个关于乾隆邀请英国钟表匠阿里斯特·考克斯制造钟表的虚构故事。
据文章介绍,兰斯迈耶被誉为“当代德语文学界的贝多芬”,获得过奥地利文学大奖、荷尔德林奖、布莱希特奖等。小说中的乾隆希望制造“永恒之钟”抵达永恒,考克斯则在制造完成后体悟永恒散置于记忆与情感绵延之中。
小说是虚构故事,当然不可以当真事,但一个托名于历史的故事,人们仍然难免要追问事情有没有一点影子。乾隆非常醉心于钟表,这是真有其事,故宫所藏钟表绝大部分来自乾隆年间;乾隆时期延请了多位外国钟表师,这也是事实。
乾隆对钟表的喜爱,估计超过任何一位君王。在他20岁还没有当皇帝时,就表现出对“精巧绝伦疑鬼工”的钟表写诗颂赞,说钟表有“考时定律佐三农,此钟之利贻无穷”的作用。54年后,乾隆再次咏赞钟表,多了一分观赏把玩的心态。乾隆除了接受外国进贡钟表,亲自把关采买、定制钟表,还在宫中设立了“做钟处”。
西方钟表匠进入清朝宫廷,远在顺治五年(1648年)就有,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全部离开,共有150多年,以乾隆时期为数最多,历史记录和档案记载中没有英国人。乾隆时期服务于宫中钟表制作的西方钟表匠都是传教士,有瑞士人林济各,法国人沙如玉、杨自新、席澄源、汪达洪、李俊贤、巴茂正、高临渊,意大利人李衡良、德天赐等。乾隆与英国人的交集,最著名的就是马戛尔尼使团,使团礼物中有钟表。
乾隆是很有“历史感”的皇帝,非常在意留下千秋英名,自我总结为“十全老人”,一直致力于把自己塑造成“古今帝王第一”。但乾隆不是一个追求自身永恒的人,而且颇为“知止”。在位六十年,因不敢超越康熙在位时长而退居太上皇。乾隆没有过求仙访道,没做过追求不老之法、不死之药的乖僻举动。
《时间的进程》作者在小说后记中表示,小说中的人物是他通过虚构历史,重新演绎世俗权力与时间的争持,实现追问人类有限性特征与渴慕永恒的宏大叙事,表明任何形式的权威终将无法逃脱时间法则的约束。这个立意不错,也不出奇,但假托乾隆来展开故事,仍然不免架空过甚、假托非人。
《时间的进程》写乾隆意欲主宰时间,提出制造“永恒之钟”,一台不用任何进一步人为的帮助就能计量和显示它的制造者及其世世代代的生命与死亡的每时每刻,直到无法想象的遥远未来。但当这台钟被制造出来后,乾隆没有启动它,就此宣告了权力的永恒无效。而在另一端,钟表匠考克斯通过对死去妻子与女儿的记忆,实现了对时间之痛的疗愈,表明爱与回忆才为“瞬时的短暂性赋予了时间长存性”。指向未来的永恒,与指向过去的回忆,在现在纠缠拉扯,而最终回忆才是时间有限性这一焦虑的药,机械时间、物理时间不是真正的时间,时间存在于个体感知和意识之中。
这个虚构故事以假托历史面目呈现,但从介绍看基本上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哲学寓言。就哲学观点来说,可以说新意有限。从奥古斯丁、康德直到伯格森,以及胡塞尔、海德格尔,都在时间属于人、存在于人的内在意识之中这一面向上作出论述。
从柏拉图以来,哲学家就划出了时间与永恒的界线。生的对面是死,时间的对面却不是死而是永恒。生死都是时间的一部分,是时间现象,而永恒不是,它超越了时间。时间是变、是有限、是不完美,而永恒不是,它是静止、是无限、是完美。永恒意味着时间不复存在、历史就此终结。
乾隆是否能从哲学上来看待时间与永恒,未必,但作为一个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人,他对“时间的进程”应该有明确的了解。知道生命的局限性、时间的有限性,顺应生老病死的规律,“不语怪力乱神”,“不打诳语”,不做永生的痴梦、不生永恒的幻想,这些对乾隆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无须经过哲学思辨才能得出结论。
有新意的是,一个奥地利作家在展开他的时间故事,表达他的时间观念时,选择了乾隆与英国钟表匠作为主人公。想来,讲述一个权力与时间、钟表的故事,放在18世纪那个机械论世界观盛行的时代较为适宜,而乾隆对钟表的喜爱估计超过了任何一位君王,英国则是那个时代钟表业最发达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