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青,2024年9月于四川安岳半边寺石窟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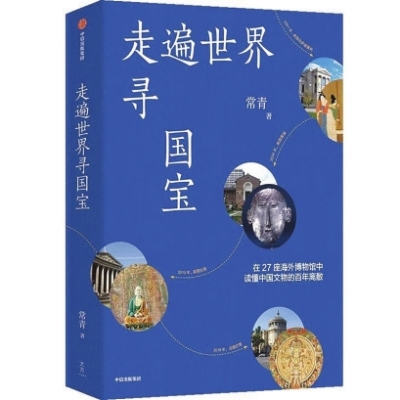
《走遍世界寻国宝》
常青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国立美术馆藏清代诰命龙凤冠。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北魏正光五年(524)金铜弥勒佛像(1924年河北定县出土,高76.8、宽40.6、厚24.8厘米)。

大英博物馆藏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之“冯婕妤挡熊”(唐代摹本)。
□ 长江日报记者 马梦娅
文物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据不完全统计,西方公共博物馆中共收藏了约164万件中国古代艺术品,这只是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20%左右,其他80%的海外中国文物则收藏在私人手中。
从大英博物馆的敦煌绢画,到巴黎吉美博物馆的佛教雕塑,再到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吐鲁番壁画,它们是怎样流落他乡的?它们如何在异国的博物馆中继续讲述着中国的故事?近日,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青出版新书《走遍世界寻国宝》。书中讲述他如何用30多年时间,探访全球50余座重要文博机构,为上万件流失文物做记录档案的故事。
《读+》周刊记者专访常青,他表示,将继续探访更多国外文博机构, 为漂泊的文明碎片 “建档立传”。通过记录、研究、传播,常青让这些漂泊的国宝始终与母体文化保持联结,为当代文化传承提供“知来处、明去处”的根基。
■ 当年以25英镑出售的国宝
流失之殇,感同身受。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常青一次又一次踏上寻访海外流失国宝的征程。
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赛克勒厅,常青长久伫立在《孝文帝礼佛图》浮雕前。这幅来自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北魏杰作,记录着一段往事:1934年,大都会东方艺术策展人普爱伦与北京古董商岳彬签订契约,以1.4万银圆收购此浮雕。岳彬转包给洛阳商人马龙图,马龙图又雇用当地保长王梦林。最终三名石匠被持枪胁迫,趁夜色盗凿国宝。他们先敲下孝文帝与其他供养人头部,再切割身子,残片经北京转运纽约。如今,浮雕上的切割痕迹仍清晰可见。
在大英博物馆进行探访记录时,常青站在有1500多年历史的《女史箴图》面前,感触颇多。谁能想到,这幅被乾隆皇帝深爱的珍品当初走进大英博物馆时,仅被售卖了25英镑。
《女史箴图》是一幅绢本设色的长卷画,内容来自西晋时期的诗文《女史箴》。诗文的主要内容是告诫宫廷女子,该如何尊崇妇德。现存于世的《女史箴图》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大英博物馆藏本(可能是唐代摹本),另一个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宋代摹本)。其中,大英博物馆藏本因保留了更多早期绘画的风格特征,被认为是最接近顾恺之原作面貌的摹本之一。
画中线条如“春蚕吐丝”般纤细流畅、连绵不断,人物造型秀骨清像,神态庄重含蓄,将魏晋时期追求神韵、注重内在气质的艺术风尚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清朝,这幅画卷是乾隆皇帝的案头爱物。乾隆皇帝对这幅《女史箴图》非常喜爱,在1746年将其重新做了装裱。他把《女史箴图》和传为宋代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并称为“四美”,藏在紫禁城内的静怡轩。乾隆皇帝在《女史箴图》上盖了37个收藏章。慈禧太后执政时期,《女史箴图》被移往颐和园。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逃往西安。当时驻扎在颐和园的英军第一孟加拉骑兵团的克劳伦斯·A.K.约翰逊上尉(Captain Clarence A. K. Johnson,1870—1937年)趁乱将《女史箴图》盗走。据约翰逊上尉家人的说法,《女史箴图》是一个被约翰逊救过的贵妇人赠送给他的。约翰逊于1902年回到伦敦后,由于他并不懂《女史箴图》的价值,仅以25英镑的价钱就把《女史箴图》出售给了大英博物馆。此画卷随即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位列BBC《展示世界历史的100件文物》第39名。
如今,它静静地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既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也是一道醒目的伤痕:有些国宝的历史,不仅刻在笔墨里,更刻在颠沛的命运中。
■ 他呼吁建立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资料库
在全球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常青有不少难忘的经历。
在美国做博士后时,常青想调查大都会博物馆里所有佛教造像,一位策展人告诉他,除了展厅和常规库房,还有些藏品放在特殊地方。之后,他竟带着一位管道修理工领常青前去。
原来,常规库房放不下那些超过一米五的大型中国石雕、造像碑,这些宝贝被存到了地下管道区域。他和工作人员揭开井盖,顺着台阶往下爬,打着手电筒才能照亮环境。常青说,在拍摄记录时,由于这些大型石雕佛像和造像碑都在地上躺着,他不得不跨在石雕上面拍照。“看着北魏、唐代的石雕就这么被随意放置,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为这些珍宝感到惋惜。”
还有一次,他在佛罗里达博物馆做策展工作。那里亚洲藏品很少,中国文物也就几百件。常青建议馆长联合当地收藏家借展,联系到近30位收藏家,并成立了一个“亚洲朋友会”(Friends of Asian Art)。其中一位医生的收藏让他震惊,单是明清字画,他就有400多件,包括祝枝山等人的作品。此外,他还收藏了潘天寿、齐白石等名家的作品,整体数量甚至超过不少博物馆。
这些经历让常青真切感受到海外中国文物分布的复杂,也让他对这份搜集工作有了更深的感触。
除了不遗余力地去做文博机构的文物记载之外,2017年,常青还做了一件特别的工作。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很多西方人在中国游历时拍了不少照片,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美国的艺术品收藏家弗利尔在1910-1911年间考察开封、巩县、洛阳和杭州的古迹之时,在中国聘请了一位名叫周裕泰的专业摄影师,帮他拍了很多黑白干板照片。这批照片极具历史价值,可以作为历史文化遗产。
在时任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档案部主任霍大为(David Hogge)先生的帮助下,常青系统地整理与研究了这批照片,写成了《物华旧影:1910—1911年弗利尔镜头里的中国文化史迹》一书,于201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探访海外中国文物,需要耗费一个人一生的精力。”常青在《走遍世界访国宝》后记中写道,“其实以一生精力也远远不够,但坚持不懈才能有所收获。”
常青说,一个人毕生的努力是为了唤起更多人的关注。他呼吁中国应建设一个覆盖全球的海外流失中国文物资料库,积极与海外文博机构定期联系,扫描、采集文物数据并录入数据库。这样的资料库能全面呈现海外中国文物在地理分布、收藏主体等维度的情况,追踪文物的流转轨迹。目前虽有个别领域或类别(如敦煌相关文物)已建立部分数据库,但建立全球性的海外流失中国文物资料库,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专业团队的持续投入和长期坚持。
这项工程或许漫长,但每一份数据的录入,都是在为漂泊的文明根系搭建坐标。当个体的坚持汇聚成群体的行动,当零散的记录凝结成系统的档案,我们才能真正握住文明传承的脉络。
【访谈】
■ 用30多年去探访,为文明碎片“建档立传”
读+:是什么促使您关注“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这一课题?
常青:我关注这一课题,其实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
1991年,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交换学者去了日本,参与奈良西大寺的发掘,其间参观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等地方。在那里,我看到了很多中国的东西,如绘画、佛教雕塑,还有一些来自唐代长安的藏品——因为我老家就在西安,所以对这些格外感兴趣。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海外收藏的中国及相关文化文物,心里受到了不小的触动。
尤其是我在奈良国立博物馆亲眼见到唐代金银平脱琴、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凝视来自龙门石窟的石雕菩萨头像时,我发现,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数量之巨,远超国人想象。
1999年,因为学习和工作的关系,我前往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研究那里收藏的中国佛教雕塑。
我花了两年时间调查,做了16万字的记录,后来在2015年整理成32万字的著作,在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段经历让我对海外中国佛教雕塑的收藏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我申请了美国国家美术馆的资助项目,想把研究从弗利尔美术馆扩展到全美国的中国佛教雕塑收藏。在那4个月里,我跑了旧金山、纽约、芝加哥、堪萨斯城、波士顿等地的七八个重要博物馆,掌握了美国收藏的中国佛教雕塑精华。
2001年起,我利用生活、工作、旅游的机会参观了越来越多的博物馆。例如,在2001年去了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通过同行、朋友的帮助,有机会进入库房看珍贵的藏品。这些参观,使我进一步了解到其他国家的中国文物情况,研究范围也扩展到了美国以外的北美地区。
2005—2006年,我在大都会博物馆做博士后研究,拍摄了馆内大量的中国物品,不只是佛教雕塑,还有瓷器、铜器等,也让我从单纯研究佛教雕塑扩展到更广泛的海外中国文物。
此后,我在美国的一些博物馆做过策展人、研究策展人等,独立策划了七个关于亚洲艺术的展览。其间也在调查中国文物。从2018年至今,我在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工作,这是我调查海外收藏中国珍宝的新的高峰。我作了两次环球旅行,访问了瑞典、荷兰、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地的重要博物馆,考察与记录了这些博物馆内展出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包括很多独一无二的珍品,它们都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珍贵的资料。
今年我出版的《走遍世界寻国宝》只是记录我研究探访工作的一个段落。我计划继续对欧洲、澳大利亚等地的海外中国文物进行普查,还会有一些关于“藏在海外的中国文物”的写作计划。
读+:有人评价您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让国宝“回家”,请问具体是怎么做的?
常青: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球47国200余家博物馆藏有164万件中国文物,而我通过实地核查发现:这仅是冰山一角——公立机构藏品只占流失总量的20%,其余80%散落在全球私人藏家手中,如同坠入深海的珍珠。
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佛教艺术,但在探寻过程中,我发现除了佛教艺术品之外,有太多的中国珍宝流失在海外。我的想法越来越明确,我想尽可能地调查搜集流失在全世界的中国珍宝。
30多年来,我探访过全球50余座重要的博物馆与文博机构。每到一处,我都会带着相机和笔记本,像对待珍宝一样记录下每一件文物的细节——从它们的来源、捐赠者到铭文的内容,再到展签上的年代标注,再一一拍照存档。回到住处后,我会连夜整理这些素材,按文物类别、年代、出土地域建立详细的电子档案。如今,我电脑里的文件夹很多,粗略统计下来,差不多积累了上万件文物的影像与文字记录。每一个文件名背后,都是一段跨越山海的寻访记忆。
海外藏有的许多壁画、碑刻、造像,都是解开佛教艺术史谜题的关键。比如面对一幅来自中国寺院的壁画,我会反复比对线条的运笔方式、色彩的矿物成分,结合相关经卷记载考证其创作背景;遇到一块流失海外的石窟造像残件,我会研究其年代、历史背景,探究它在原窟中的位置与整体风貌。这些细致的考证与辨析,希望能为学界填补某些研究空白。
许多流散在异国他乡的文化遗产,国内民众难有机会亲眼看见,我想把这些文物的故事带回国内。无论是伦敦大英博物馆里的商周青铜器,还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宋元书画,我想尽力系统整理它们的流传脉络、艺术特色,通过展览策划、书籍出版等方式,让更多人知道这些“游子”的现状,唤起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珍视。
而且,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应只停留在论文里,不应只面对学术圈的少量受众。我尝试用更通俗的方式解读这些文物:例如举办通俗讲座,出版通俗读物(如《中国石窟简史》),给学生或者文物爱好者讲解历代造像之美,让艰涩的专业知识,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传播的内容。
■ 不止于“国宝回家”,以开放心态看文明链条
读+:散落在世界的中国文物具体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它们因为哪些原因流失海外?
常青: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文物,从地理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其中美国是大头。若将全球欧洲、美洲和日本的中国文物总量算作5份,美国大概占3份。
从收藏主体来看,可分为公共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两部分。目前已知公共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约有160多万件,这只是很小一部分,更多的文物在私人收藏家手中。据不完全统计,海外私人收藏的中国文物将近800万件,加上公共博物馆的,总数有上千万件。
很多中国人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参观时,看到中国艺术品第一个反应是:这都是美国人参加八国联军时抢走的。我想辟个谣,大都会的中国藏品大多数是私人捐赠的,有的则是由馆里的策展人用私人捐赠的钱购买的。其中最不光彩的一件事就是该馆东方艺术部策展人普艾伦在20世纪30年代雇中国古董商盗凿了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北魏的《孝文帝礼佛图》浮雕。
2018年深秋,我在纽约“亚洲艺术周”的一家古董店发现了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北魏大臣头像,就来自《孝文帝礼佛图》。“亚洲艺术周”之后,这件珍品已被人买走,消失在私人收藏的迷雾中。大多数私人藏家普遍不愿透露收藏信息,除非文物被博物馆收藏并展出。这是很无奈的事。
要弄明白这些文物流失海外的原因,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清朝末年与民国初年,社会不断动乱,清朝八旗子弟贵族失去了生活来源,只能变卖家中传承数百年的古董;同时,中国动乱导致很多家庭破败,也不得不出售家中物品。而当时中国人购买能力低,外国人便趁机收购。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开租界,加上19世纪末西方掀起中国文化热,汉学家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引发了外国人对中国文物的兴趣,很多人看到商机,中外古董商便大量贩卖中国文物到国外。
这些文物中,只有少数是由博物馆资助的策展人或学者直接带入博物馆,绝大多数先流入私人收藏家手中,之后不少收藏家会在去世前通过遗赠的方式捐赠给博物馆。西方的很多博物馆也是私人捐赠的,就像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便是以捐赠者名字命名的。私人收藏家的不断捐赠,才会使大量文物最终进入公共收藏领域。
读+:中国人都盼着国宝能回家,您以及相关研究者所做的文物记载追索工作,对于推进海外流失国宝回家有怎样积极的作用?我们应如何看待“国宝回家”?
常青:我们做的这些工作是“国宝回家”的基础支撑。研究者通过调查海外藏品,梳理文物的年代、来源和流转脉络,能为追索提供关键依据。比如通过比对海外造像与国内同期文物,明确其出自特定墓葬或石窟,就能为依法追回提供确凿证据。同时,系统记录海外流失文物的信息,能让我们清晰掌握国宝在何处,为后续的追索行动划定范围、找准目标。此外,这类研究还能通过学术层面的论证,让国际社会更认可文物的归属价值,为跨国追索营造更有利的舆论和认知环境。
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制定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该公约仅对缔约国生效后的非法进出口行为具有约束力(即各国批准公约后发生的非法行为需承担义务,通常从批准日期起算)。公约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一,其效力依赖缔约国国内立法落实,而部分主要文物市场国初期未加入或执行力度有限(如英国2002年才加入);其二,公约明确不溯及既往,对于生效前(或缔约国加入前)的文物非法流出,通常难以直接依据公约追索,但部分国家可通过国内法、双边协议或其他国际机制主张权利。
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看待国宝回家需要理性与包容并存。一方面,国宝承载着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期盼它们回归是自然的情感流露,这种情结背后是对自身文化的珍视,值得肯定;另一方面,也需认识到文物追索受历史背景、国际法律和现实条件的限制,并非所有流失文物都能短期内回归。更重要的是,比起单纯纠结“是否回来”,更应关注对流失文物的研究与认知——了解它们在海外的保存状况、研究它们所承载的历史信息,这同样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真正的文化自信,既包括让流失文物回家的努力,也包括以开放的心态研究和传播自身文化,不因文物暂处海外而忽视其价值。
每一件流失的文物都承载着特定时代的技艺、审美与社会记忆,知晓它们来自哪个朝代、出自哪些工匠之手、曾见证怎样的历史场景,不仅能还原文物本身的艺术价值,也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化发展的完整链条。从当代文化传承来看,“知来处”是为了锚定文化的根脉。唯有清楚先辈创造了怎样的文明,我们才能理解我们是谁、从何而来,这是文化自信的源泉。
“明去处”是明确这些文物如今藏于何处、如何被展示、又在向世界传递着怎样的中国故事,知道这些国宝在海外的角色与影响,才能更主动地推动文化传播与交流,让传统在当代焕发新生。
“知来处,明去处,建档立传”的意义,不仅在于记录,更在于唤醒。通过系统地整理研究,还原文物本来的文化语境,让它们重新“活”起来,照亮它们的前世今生。知道它们从何处来,才能明白它们该往何处去。这种文化自觉,正是文明传承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