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菲利普·鲍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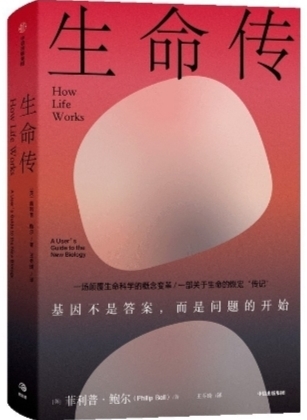
《生命传》
[英]菲利普·鲍尔 著 王乔琦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上周,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英国学者菲利普·鲍尔,他的新书《生命传》系统地挑战了过去几十年深入人心的“基因决定论”,指出DNA不是“生命蓝图”,基因也不是“生命说明书”。鲍尔是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员、欧盟委员会合成生物学专家团成员,曾任著名科学期刊《自然》编辑20余年,著有20多部科普作品。
■ 鲍尔迎来“黑客帝国”时刻
鲍尔应该是个电影爱好者,他在《生命传》里多次引用各种电影桥段。“20世纪90年代,我在科学期刊《自然》担任编辑。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直接。我当时的感觉有点儿像基努·里维斯在《黑客帝国》中饰演的角色尼奥,因为细节上的一些矛盾之处和奇怪的事情而开始怀疑周遭世界是否真的是它看起来的样子。尼奥曾试图对这些小故障视而不见,但他一旦开始直面它们,就必然会改变自己对事物运作方式的看法。说回我自己,在《自然》每周的编辑例会上,生命科学团队的同事们不时就宣布接受了一篇论文。这类论文的内容基本就是证明人们常常认为参与功能Y的基因X对现象Z同样重要。我当时是物理学编辑,对生物学一窍不通,总是会怀揣极大兴趣聆听他们的发言,但最后一点儿也没懂。最后,我鼓起勇气发问:‘所以,这有什么意义?’而他们总是会以高兴的口吻回答:‘我们也不知道!’”
按照当时流行的“基因决定论”,基因应该对应明确功能,基因图谱就像人体说明书。可是相反的案例不断出现,wg基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果蝇胚胎因为wg基因突变缺失了正确的体节,就不能发育出翅膀,这项研究赢得了199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问题是,小鼠体内也有这种基因,其功能是很容易引发癌症;而且人类也有19种类似基因。
那么,该基因的真实功能到底是什么?
鲍尔打了个比方,这就像是问“in”这个词有什么含义。字典的定义是“表示某物的位置状态是被其他事物或看似被其他事物包围或环绕”;然而更恰当的说法是:“in”的具体含义取决于上下文。比如I put my foot in my mouth(我说错话了)、He’s one of the in crowd(他是圈内人)、In spring it rains(春天会下雨),以及Come in(进来)。
鲍尔就这样产生了对“基因决定论”的怀疑,这怀疑如同冰面的裂缝,越来越大。
2000年6月26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人类基因组草图完成,称“我们正在学习上帝创造生命的语言”。这一宣告标志着“基因决定论”叙事的巅峰。《生命传》一开笔就写了这一幕,然后给出一句评语:“他错了。”该计划最初预测人类拥有5万—10万个编码蛋白质的基因,然而2003年公布的最终结果显示,这一数字仅约2万个,与线虫、果蝇的基因数量相差无几。这个“基因数量悖论”直击基因决定论的要害——若基因是构建复杂生命的“蓝图”,如此有限的基因储备根本无法支撑人体精妙的生命活动。
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20余年,临床医学获益却相对很少,心脏病、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复杂病症仍无法通过“读取基因”精准预测或治愈。当生物学家被问到“为什么”时,他们通常会表示,解码基因组比预想的复杂得多。
当初可不是这样的!“基因决定论”最强势的那些年,某位遗传学家喜欢在做讲座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装满基因序列信息的光盘,然后对听众说:“这就是你。”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的网站则声称,人类基因组是“大自然建造人类所需的完整基因蓝图”。各路人马一拥而上,声称发现了“暴力基因、名人基因、懒人基因、犯罪基因”,DNA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一种象征,几乎有了宗教般的魔力,潜力无穷、商机无限!
鲍尔回顾了这一幕,然后继续反击。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流行一种“基因敲除”技术,就像是一个接一个地替换电路组件来查找哪里出了故障,问题是,基因敲除实验的结果往往让人摸不着头脑,基因X似乎绝对是生物体正常运作的核心,等到敲除它后却发现没有任何明显的影响,整个生物体看上去仍旧非常健康。
■ 把生命比作机器是一种贬低
那么,生命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呢?
1982年,英国神经外科医生为一名头部异常肿大的6周大的婴儿做了脑部手术。在大脑的脑室内,医生发现了一个14厘米长的胎儿,已经发育出了头、躯干和四肢。医生将其取出后,患儿康复了。
这“胎中胎”听起来怪诞,鲍尔认为,这恰恰证明:发育不是预设程序的展开,而是一套容错、开放、多路径的生成系统。
英国演员皮尔逊和他的同卵双胞胎兄弟均携带NF1基因突变,但一人面部严重畸形,另一人近乎正常,鲍尔认为,这说明发育历史与随机性的作用。
鲍尔的反思和追问最终指向现代科学两大深层范式——机械论与还原论。鲍尔指出,“生命是机器”的观念可追溯至笛卡儿,在20世纪分子生物学兴起后,这一隐喻尤其体现在“基因是蓝图”“细胞是工厂”等流行叙事中。还原论则主张将生命拆解为分子、基因等微观组件,认为“理解组件即可解释整体”,这一思路推动了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但也造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知盲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困境,证明了还原论的无力;而生命中的“涌现”现象,更是还原论无法解释的。
他的质疑最终指向一个更谦卑也更真实的生物学愿景:放弃“蓝图”幻想,拥抱生命作为过程的复杂、稳健与创造力。他写道:“把生命比作机器、机器人、计算机,都是对生命的贬低。我们之所以很难准确理解生命,正是因为生命与我们创造的这一切都不同。当我们忘记这些比喻的局限性时,对科学的应用会陷入困境。例如,我们可能会寻求不恰当或者根本无效的医疗干预。以机器比喻生命的根本问题在于,它迫使我们把生命的各个组成部分看作具备特定功能的东西。我们会拿起某个组件,然后问:这部分发挥了什么作用?”
鲍尔认为:生命是过程,不是物体:发育是稳健过程,允许多路径达成同一吸引子状态;生命体具有感知、目标与适应能力;生命的本质不是分子的简单叠加,而是“能从环境中挖掘意义、自主追求目标”的系统——从细菌寻找营养,到人类产生情感,都是生命“能动性”的体现。这种能动性源于分子网络的自组织、细胞的集体决策,以及多尺度系统的协同作用,最终让生命在混沌的分子世界中,构建出有序、稳健且充满适应性的“活”的状态。
当公众仍在争论“先天与后天”“基因与环境”时,鲍尔指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生命不是基因与环境的简单加和,而是多层次互动的动态过程。
当医学界执着于“靶向治疗”“精准医疗”时,鲍尔提醒:疾病不是零件损坏,而是系统稳态失衡。癌症不是基因突变的线性结果,而是吸引子状态的病态锁定。
当合成生物学试图“编写生命程序”时,鲍尔警告:我们无法像编程计算机一样编程生命。
更重要的是,《生命传》让我们重新敬畏生命的复杂性与创造力。在一个崇尚“简洁叙事”的时代,鲍尔勇敢地说: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供我们寻找生命运作方式的答案。生命是一种多层级过程,每个层级都有自己的规则和原理:基因有基因的规则,蛋白质有蛋白质的规则,细胞、组织及其他身体模块(比如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也各有规则。对生命来说,这些规则都不可或缺,而且没有优先级、重要性之分。只有在这种层级结构中才能找到复杂生物功能的起源与解释,生命生来就与“众多”二字联系在一起。
或许,这才是对“生命如何运作”最诚实的回答。
【访谈】
■ “自私基因”已被主流学界拒绝
读+:《自私的基因》在中国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来自“基因决定论”,也来自“自私”。很多人认为这揭示了生命的终极目标,那就是复制自己、传递给后代。我看到一些书,他们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人的情感、本能、社交行为、恋爱、婚姻甚至经济活动。现在,你否定了“基因决定论”,但是“自私”是否仍然成立?
鲍尔:所有生物都有一种倾向,即寻求能够帮助它们生存和繁殖的行为策略(当然了,有些人会选择不这么做)。在进化生物学中,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倾向源自基因——毕竟,通常被复制的并非生物个体本身,而是基因。这种思考进化的方式极其有用。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因此称基因是“自私的”。一个生物体内的所有基因必须协同合作,才能实现繁殖,从而完成基因自身的复制。事实上,理查德·道金斯也说过,他这部最为出名的作品也可以叫作《合作的基因》。
理查德·道金斯写道:“我们生来自私。”因为自私就扎根在我们的基因里。他还补充说,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要努力宣扬慷慨和利他主义”。
然而,基因真的自私吗?要是顺着字面思路,批评基因不可能是“自私”的,就像它绝不可能是“快乐”的或“固执”的一样,就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因为基因没有情感、没有目标,也压根儿不是真正的生命。
真正应该讨论的问题是,这个比喻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有些人认为,基因组包含了一大群基因,这些基因以符合达尔文学说的方式相互竞争。可事实恰恰相反。编码某种蛋白质的基因压根儿不会与编码另一种蛋白质的基因竞争,我们绝不会看到生产乳糖酶相关的基因试图“战胜”与生产氢化酶有关的基因。相反,如果某个基因发生的某种突变提升了携带这种基因的生物体的生存能力,那么这种突变基因很有可能会在整个种群中传播,让其他不那么成功的等位基因黯然失色。
毫无疑问,基因(这里可以更具体地指等位基因)提升的是整个生物体的生存能力。它绝对没有办法在不造福其他基因的前提下,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这是“自私”吗?
另外,“自私的基因”指的是进化视角下的基因,而给发育生物学视角下的基因贴上“自私”的标签几乎没有意义。为了让生物体正常发育,特定基因组中的基因几乎必须协同发挥作用。因此,公正的说法应该是,同种基因的不同等位基因相互竞争,同属一个基因组的不同基因则相互合作。前者是进化叙事,在进化的时间尺度上展开;后者则是发育叙事,在生物体的一生或是妊娠周期内展开。
我们可以将某种基因的成功变体(称为“等位基因”)在种群中扩散、排挤其他较不成功等位基因的现象,视为“自私”的表现。这正是自然选择的核心机制。换句话说,并非不同基因之间相互竞争,而是同一基因的不同等位基因之间存在竞争。然而,“自私基因”观点的支持者常常未能清晰区分这一点,从而导致公众产生误解。
我认为“自私基因”观点的问题在于,它暗示基因是“掌控者”,似乎基因决定了生物体的一切行为。这显然是错误的,在生物学中,基因很少真正成为性状或行为的直接“原因”。如今,随着我们对基因功能的理解日益深入——尤其是在人类这样的复杂生物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基因更应被看作是生命体(及其细胞)在维持生命过程中所利用的资源,而非发号施令的“指挥官”。
我还要澄清一点: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并非我个人独创、与“主流基因理论”相悖的理论。相反,我所呈现的,其实是当今许多进化生物学家、发育生物学家和细胞生物学家普遍持有的遗传学与生命观。“自私基因”这种简化论的观点,在当今生物学界其实并不被广泛接受——尽管每位生物学家可能都有自己表达“事情远比这复杂”的方式。因此,我不认为我的书与生物学主流思想相冲突;恰恰相反,我写作此书,正是为了梳理并整合过去二三十年来细胞与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些进展已经彻底改变了20世纪70至90年代那种对基因、生物分子和细胞理解尚浅的“旧图景”。
■ 永远无法通过基因编辑来制造更聪明的婴儿
读+:你在书中提到了电影《千钧一发》(1997年的科幻电影,讲述在未来世界,主角因“自然出生”未经过基因优化只能当清洁工,他借用基因优化人的血液、尿液、毛发,改变身份进入太空——《读+》注),我对那部电影正好印象深刻。很多人都对那种未来感到恐惧。在你看来,如果人们对生命的复杂性有更加深刻的认识,那是否意味着,测量人的身心,以此决定其获得的资源、发展的路径乃至一生的命运,那种可怕的前景变得不大可能了?
鲍尔:我们无法仅凭一个人的基因组序列就准确预测他/她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我们确实可以依据基因信息做出某些预测——例如,此人对某些疾病的易感性。我们也可以基于这些数据做出概率性估计,比如他/她可能的身高,甚至可能的智力水平。
但这些预测始终只是概率性的。因此,这类预测可能带来危险。例如,如果在体外受精过程中对胚胎进行基因测序,并据此让父母相信孩子将来一定会如何,而孩子实际表现却与预期不符,父母的期望就可能被扭曲。更糟的是,如果我们试图通过基因编辑“编程”出某些被认为理想的性状,不仅通常无法确保这些努力会按我们期望的方式奏效,还可能无意中引发其他意想不到的改变。
对于少数由单个基因主导的疾病(如囊性纤维化或镰状细胞贫血),通过基因编辑预防疾病是可行的,也可能带来巨大益处。但这些只是例外。我认为,我们永远无法通过基因编辑制造出“更聪明的婴儿”,因为生物学根本不是这样运作的,并不存在可以独立发挥作用的“智商基因”,许多智商相关的基因必然也与其他性状(或许是神经质或精神分裂症)相关。因此,我们如果以这种方式筛选胚胎,就很难知道同时还筛选出了什么其他性状。
公众必须理解这一点,因为我担心会有公司作出误导性的承诺。此外,抛开科学可行性不谈,试图在基因层面“设计”婴儿还涉及诸多伦理与社会问题。
读+:有很多超级富豪对“人体强化”很感兴趣,试图让自己更强壮、更聪明、更长寿。《未来简史》中预言,富人有能力利用基因编辑等技术改造自己和后代,成为拥有超能力的“类神”,而普通人则因无法使用这些技术,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将加剧社会不平等。如果“基因决定论”被质疑和否定,这是否意味着富豪们的计划不大可能成功?
鲍尔:是的,基于上述原因,许多关于“人类增强”的想法都是幻想。这未必能阻止富人尝试,因为许多极度富有的人生活在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世界中。但我们不应让科幻小说中的构想主导我们的思考;在讨论伦理上“应不应该”之前,我们必须先厘清科学上“能不能”。
读+:今天,世界上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基因产业,产业似乎乐于制造和维持关于基因的“神话”。现在你质疑这神话,你认为基因产业的未来会是怎样?
鲍尔:我毫不怀疑,一些“基因筛查”和“基因编辑”公司会做出缺乏科学依据的承诺——这种现象已经出现。许多科学家已在警告这些问题。因此,各国亟须制定相应法规。2018年,贺建奎对两名女婴的基因进行了不道德且实际上不必要的编辑,最终因违反相关规定而入狱,这正说明了监管的重要性。当然,任何规则都无法完全杜绝个别人违规,但它们至少划定了科学与社会可接受行为的边界。事实上,科学家普遍欢迎清晰的法规,因为这让他们能明确知道哪些研究可以开展,哪些不可以。同时,我们也必须确保这些规则、法规和指南不会过于严苛,以至于阻碍了潜在有价值的研究和生物医学干预。这些规范的制定,应通过科学家、政策制定者、伦理学家、法律专家以及公众之间的广泛对话来完成。
■ “生命”是最难写的一本书
读+:把整体事物一步步还原为部分,并分析每个部分的作用,这种“还原论”在科学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在今天也依然是重要的方法;你是否认为,有一些科学领域,比如生命科学这样的复杂系统,不能单纯依靠还原论?
鲍尔:我不喜欢把“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简单划分为“还原论”与“整体论”两种对立视角。在我看来,显然两者都需要:我们既要理解分子层面的精细细节,也要明白生命并非只是把这些零件拼凑起来那么简单——它是一个真正涌现的过程,远大于各部分之和。更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部分与整体”的问题。生命具有层级性:它包含多个层次,每一层都有其自身的规则。我们在许多非生命系统中也能看到类似现象(比如天气或大脑)。
还原论不能算优秀:它是一种坚实可靠且极其有用的方法论,但只是罗列各种生物组件,无法揭示真正的生命运作机制。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深刻反思生命运作方式的起点。生物学从来就没有简单过,总是会有各种例外、复杂情况和棘手的细节,任何论断都可能招致来自某个方向的反对乃至愤怒。或许,唯一一个没有任何争议的论断就是:生物学仍然有太多内容是我们未知的。
读+:你是物理学博士,你写的书涉及化学、分子科学、艺术史、中国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生命传》则属于生命科学领域。当你思考“生命如何运作”的时候,这种宽广的知识面给了你什么样的影响?
鲍尔:作为一名化学家,我在探讨分子生物学细节时感到得心应手。但我也意识到,我们必须正视分子世界的真实面貌——它充满“噪声”、随机性和杂质。因此,那种认为生物分子只是被简单“编程”去执行特定任务的简化观念,不足以真正理解生命。
而作为物理学家,我受过训练,习惯于寻找问题背后的“物理原理”——即系统运作的一般规律。物理学也让我熟悉了分子间的协同过程:我们必须关注整个系统的动态,而非孤立地看待单个分子。人们常误以为物理学是最“还原论”的科学,但这其实是对现代物理学的误解。现代物理学同样关注集体行为与涌现现象,而这些正是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的核心。
我想说的是,我在其他著作中一贯的思路,就是试图全面审视所探讨的主题。在《生命传》一书中,这意味着我必须思考该问题更深层的哲学层面,包括能动性与因果关系等议题。除非我们愿意这样做,否则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生命。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我写过的最难写的书。
(注:本次采访通过电子邮件以英文进行,由AI协助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