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蒯乐昊
云冈石窟是北魏时期由皇家开凿的石窟群,是中国石窟艺术宝库中不可错过的瑰宝。
《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是关于云冈石窟与历代云冈人命运交织的非虚构作品,爬梳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亦讲述了无数云冈人的故事:一举夺回学术主动权的中国云冈学奠基人宿白先生,勇敢开辟新赛道的云冈守护者、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用古建筑学思路还原石窟工程营造的新一代学者彭明浩,保护石窟的文物医生们,努力留下石窟今日样貌的数字化采集工作者们……
这本书用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故事带领读者从北魏王朝走到AI时代,这是1500年的云冈。
■ 打破关系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第一次来到云冈,是在1993年。当时,他还只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一名硕士生,来云冈做实地调研,为写第20窟做准备。他师从宿白先生,当时宿先生正在为他们讲授中国美术史的专题,尤其指点他们要学习借鉴日本学者著书的体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杭侃对“打破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所谓“打破关系”,是指在对遗址的考察中,发现晚期痕迹打破了早期的存留。比如体现在雕刻上,就有可能是后期的改动造成了图案对不上、图像变形、施工痕迹不合理等现象。寻找“打破关系”,有点像在遗址现场玩“找别扭”的游戏,每一处小毛病都可能是一个线头,会牵扯出后续的一系列追问。谁改的?什么时候改的?为什么要这样改?当时发生了什么?考古如破案,“打破关系”,便是真相穿越历史、传递给后世侦探的蛛丝马迹。在云冈,因为工程时间跨度长、政权沿革频繁、工匠队伍庞杂,变量众多,这种“打破关系”比比皆是,成为后世学者研究云冈石窟分期、工程营造及北魏政权的重要线索。
云冈的第20窟是云冈唯一一处“露天窟”,前窟门早已坍塌。何时坍塌?因何坍塌?日本学者推测坍塌时间不晚于辽代,但具体时间仍不明朗。杭侃推测,第20窟应该在北魏的开凿过程中就发生了坍塌,并且发生过不止一次。坍塌之后,工匠们做过补救,将断掉的西立佛残片重新接榫起来,在窟前加接了木阁。
带着他在云冈第20窟的新发现,杭侃开始着手写文章,第一稿洋洋洒洒,写了将近三万字。“当时拿给宿先生看,宿先生就叫我修改,前前后后改了好几稿,宿先生还是不让我过关。”
宿先生指点杭侃说,你抛出一个观点,要防止别人跟你商榷,你的证据是什么?后手又是什么?有些问题,并非前人没有想过,如果没有新材料,或者论据不充分,宁可不要写进文章里。
当时没有电脑,写文章得用蓝紫色的复写纸留备份,修改段落要靠剪刀糨糊来剪贴,三万字的稿子来来回回修改,过程极其烦琐。“改到最后我都犯嘀咕了,我只是想拿两个学分,我压根儿没想着要发表。”杭侃说,改稿子改到最抓狂的时候,他忍不住犯了小心眼儿,认为可能是自己的观点忤逆了导师,所以一直不得过关。
修改依然没完没了,三万字的稿子改到后来只剩下七千来字。突然有一天,宿白先生给杭侃手写了一张条子,让他把稿子拿去《文物》杂志发表。到了1994年10月,这篇名为《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的文章在《文物》刊发了,在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从那之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写文章,怎么做学问了。”
“宿白先生确实是学问大家,他不介意学生跟他观点相左,只要你能自圆其说。这也成为后来我们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一个学术传统。我的学生彭明浩关于云冈营造的理论,就比我的理论又向前走了。考古是一门不断刷新认知的学问,学生拓展、超越老师的观点,甚至推翻老师的观点,我觉得这都很正常。”
■ 数字云冈
2015年,云冈的数字化真正步入正轨。2016年,测绘学硕士李丽红来到云冈的数字化保护中心,恰好见证了云冈数字化从起步到发展壮大的过程:“石窟测绘是一个很特殊的测绘领域,精密度要求也大不一样,以前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省的测绘,它的精度达到米级、厘米级就很高了,但是对于石窟测绘来说,测绘精度起码是毫米级的,甚至我们现在都是亚毫米级的。”
云冈石窟的砂岩质地,易雕刻,也易残损风化,石质表面的砂岩颗粒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风化掉落,保护和修复虽然能起到一定的延缓作用,但改变不了岩石本身的质地。“数字化的工作就是跟时间赛跑,可能我们做得稍迟一点,它表面的掉落和变化就会让我们多损失一部分内容。”
这几乎是所有石窟寺文物工作者的共识,无论是在敦煌,还是在云冈,都能听到同样的说法:这些石窟终有一天会消失。但这并不影响敦煌人、云冈人,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石窟寺的工作者们守护石窟的决心,这些文明遗存已历经千年劫难,穿越时间,依然带着它们动人心魄的美存续到今天,今天的人就要尽量留住它在今天的样子。
莫高窟遗存以壁画为主,数字化采集工作大多是扫描处理平面二维的信息;而云冈石窟跟敦煌的情况不同,大量遗存都是高浮雕,结构立体、复杂,大大加剧了采集的技术难度。“云冈石窟的规模非常大,因此数据量也极为庞大。举例来说,光是一个第13窟,采集的资料照片就有130000张以上,差不多是17TB。”
云冈石窟现存主要洞窟45座,此外还有209个附属石窟。
“现在最大的技术‘痛点’,就是云冈中部这块,第5、6、7、8这几个窟,目前都还留着,没有做采集,这几个恰恰又是非常精彩的窟。尤其是第6窟,它窟内是一个中心塔柱,塔柱的每一个面上,都有两层帷幔,层层递进,进深特别深。但咱们采集过程中,出于对文物的保护,都严格要求‘非接触式采集’——不管你是搭作业平台也好,还是人工采集也好,全程都不能触碰到塔柱。你想,作业平台本身已经离塔柱有距离了,里面又很深,采集设备要伸进去很困难,帷幔上还有很多镂空的高浮雕,镂空部分可能只有几厘米的宽度,需要极小的设备才能胜任,市面上这么小的设备倒是有,但这种设备的精度达不到0.03毫米……”李丽红遗憾地说。在他们的设想中,可能要研发一个类似摇臂的、可以伸进去的采集设备,同时又要很小,比现有的手持设备还要小很多,近似手机尺寸,而且伸进去之后,能自行拐弯,甚至能360度旋转,并且依然要达到0.03毫米的精度,才能满足需求。
这几个窟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采集过程中,也在于采集后的数据处理。还是以第6窟的中心塔柱为例,因为塔柱的遮挡,在采集窟壁四周一圈信息的时候,视觉遮挡会导致采集数据的断裂,局部的镂空高浮雕也会造成相似的问题。几个部分的数据最后如何拼接,才能天衣无缝地“斗”在一起,也是技术难题。
云冈研究院为此专门请来测绘界泰斗级人物李德仁院士,展开现场调研。从2021年开始,云冈数字化中心与李德仁院士所在的武汉大学合作,对这几个难度超标的洞窟展开有针对性的采集方案研发。
■ AI赛道
人工智能介入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是云冈的一项新尝试。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马世长,也是宿白先生的弟子、石窟寺研究专家。他曾经做过一项系统性苦功:统计敦煌莫高窟的造像比例。因为他意识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美学特征,比如说佛像身形比例、衣纹特征等,如果有统计数据,就可以归纳出规律,作为断代分期的参考。传统考古学人的统计方法是用尺子做测绘,做记录。统计完莫高窟的一个洞窟,马世长就意识到,这将是一项海量的工程,即使敦煌的数百个洞窟能全部统计完毕,拿到数以十万计的数据,他也无从下手。
而这恰恰是大数据和AI最擅长的领域,数字化采集首先解了人力测绘统计之困,实现所有洞窟无死角的数据采集。拿到海量数据之后,人工智能就可以启动强大的算力来分析和归纳这些数据,合并同类项,对比差异项,寻找规律,形成观点。
比如他们现在正在重点研发、追求突破的第39窟聚类分析项目。第39窟里的千佛,其实在云冈是一个频繁出现的题材。云冈很多洞窟里都有千佛,所谓三世三千、十方化生,但千佛中的每一个小佛都是由工匠人工雕凿出来的,所以它注定不会像机器雕刻的那么整齐划一,不同的工匠有不同的雕刻方法,有不同的匠作传统,甚至有不同的粉本底稿,这就决定了雕出来的千佛乍一看密密麻麻都一样,但细看一定有区别。这时候,就可以用马世长先生的比例法来做研究,比如研究佛像的头身比、肩宽、身长等,用数字化采集夯实了数据量的基础,然后再让AI算法从海量数据中去提取它们的特征,做聚类分析,从而归纳出规律。
这就有可能带来很多考古学的新成果,比如仅仅是一方刻有千佛的窟壁,就有可能分析出以下信息:工匠分几组?施工的顺序和进度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匠作工艺如何?谁在雕刻这一片区,谁又在雕刻那一片区?中间是否出现“打破关系”?“打破”的原因又是什么?是否存在时代更迭?不同时代的工匠各有什么技术特点?……AI一旦大踏步介入,就会为考古学的未来打开想象的天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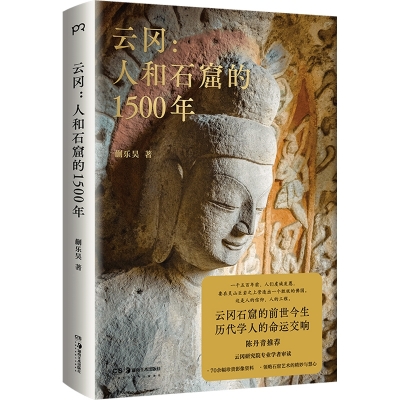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