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到来,旅游是否充满惊喜愉悦、旅程中收获怎样的独特感受,是人们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原因。如何避免“千城一面”,将一个地方打造成既有文化底蕴又有流量密码的旅游目的地,让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成为人们幸福美好生活的实践路径,是旅游策划者值得深思的事。
近日,旅游文化研究专家、复旦大学旅游学系副教授沈祖祥出版著作《我为旅游设计灵魂——文旅策划成功的秘密》,提出“旅游灵魂设计”的主导范式,成为一种文旅策划的新方法论。多年来,沈祖祥为全国300多个旅游地和旅游项目进行文化挖掘和包装,如为浙江德清县莫干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海南南湾猴岛、安吉中国竹博园等做旅游策划,赋能文旅产业。
上周,《读+》周刊专访沈祖祥,他认为“中国旅游要文化,更要灵魂”。要“找魂”:挖掘文旅基因;要“造魂”:策划精准并成型;还要“销魂”:进行营销推广。策划者为旅游设计“灵魂”,要对历史负责任、对未来有价值。沈祖祥指出,旅游的终极目的是幸福,策划者要永远以人为中心。
■ 从300多个策划案中提炼破圈密码
沈祖祥在大学读的专业是历史学,有着深厚的史学根基。他喜欢中国古代史、古典文学,爱好老庄哲学。大学毕业后,他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工作过一段时间,参与了多部历史学方面的书稿编写。从事旅游教学与研究后,他以旅游文化作为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他说,旅游和文化的关系,“好则如热恋中的情侣,不好则是反目后的情敌。”从经济和产业的角度来看,文化是旅游的资源,旅游是文化的市场,文化成就了旅游的内容,是旅游的消费品。
中国的旅游产品缺乏创新,很多项目难以打破同质化的局面,这让他思考良多。
在刚开始做旅游设计探索的时候,沈祖祥也遇到了许多问题。
他来到河南商丘。商丘是中国火文化的发源地和重要流传地,燧人氏发明的钻木取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商丘这座全国唯一四千多年没换过名字的城市,并没有因为火文化而“火”起来。
他来到昆山锦溪。有人说看过周庄又来到锦溪,有着不一样的惊艳。而他因为实在找不出锦溪这种“不一样的惊艳”,最终知难而退,退出了锦溪古镇的旅游营销策划。
他来到温州瑞安。沈祖祥承担了寨寮溪、卧龙峡、桐溪湖、金鸡山等旅游项目的策划。虽然竭尽全力演绎了卧龙故事,挖掘了养生文化,策划了活字印刷文化村,但效果都不太理想。
他来到台州临海,主持桃渚古城旅游开发策划。人们都说,桃渚古城文化“厚重”,而他感觉到的却是一筹莫展的“沉重”。
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怀疑文化在旅游中的实际价值和作用,甚至怀疑自己的历史专业特长到底能不能派上用场。
在直面挑战、甚至一筹莫展的过程中,沈祖祥开始反思并逐渐认识到,旅游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旅游中的文化问题是由个人经验的困境造成的。如果要找出旅游的文化对策,就必须重新检验文化。
沈祖祥开始尝试不停地改变自己,寻求以新的方式来缩小文化和旅游及现实之间的差异。
在海南猴岛项目的设计上,沈祖祥深入挖掘当地独特资源,将自然生态与文化特色紧密融合,打造出极具吸引力的文旅体验。
猴岛作为猕猴自然保护区,拥有独特的山海风光,森林覆盖率达95%,奇岩怪石、岩洞众多。沈祖祥秉持生态优先原则,以猕猴为核心吸引物,在充分保护猕猴生存环境的基础上开展旅游设计。比如,设置合理的游览路线,让游客能在不打扰猕猴生活的前提下,近距离观察猕猴在林间跳跃、觅食、嬉戏。
另外,他将疍家文化巧妙融入项目。游客乘坐游船环游港湾,能观赏疍家渔排独特的海上居住形式,体验拉地笼捕鱼、听疍家调咸水歌等特色活动。
如今,猴岛不仅成为众多游客喜爱的目的地,更是创造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效果。
多年来,沈祖祥为全国300多个旅游目的地进行文化挖掘和包装,在经验累积中,他愈发觉得,传统的产品已经无法满足人们需要,适应市场竞争,迫切需要把原来的产品打造成品牌,要在战略层面上做大做强。
“用历史思维解构旅游,用旅游场景重构文化”是沈祖祥要强调的关键。人们的旅游体验,终究是追求幸福感的体验,旅游的意义,正是在于通过空间的迁移唤醒这种潜藏的精神能力,让人们在“别处”发现未曾察觉的生命光彩。
【访谈】
■ 旅游地空有文化却没“魂”,就成了流水线产品
读+:请结合您的研究,聊聊中国人对旅游观念的变化。尤其是现在,人们旅游时更注重什么?和以前的体验追求有什么不同?
沈祖祥: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表面上看,人们的旅游方式变了,其实核心是中国人对旅游的认知发生了革命性转变。我研究旅游发展多年,发现真正的分水岭是1999年黄金周制度的实施——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将每年春节、“五一”和国庆节法定节日加上调休,形成了3个“黄金周”。人们有更多的假期去享受生活,体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人们对于旅游,有两个层面的转变。
首先是人们从“旅行”到“旅游”的认知质变。古代乃至改革开放早期,“旅行”的关键词是“行路难”,李白诗云“飘飘紫霞心,流浪忆江乡”,充满漂泊感。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本质是把出行当生存需求或被迫行为,比如公差、求学。现在,“旅游”的“游”字成了核心,强调玩得自在——这是从“生存型移动”到“享受型体验”的心理颠覆。
第二个变化很关键,是从“被动安排”到“主动旅游”的心态转变。以前旅游得有“正当理由”,比如去外地顺路打卡,去博物馆参观学习,参观完要写观后感,带着任务去做这件事。现在呢?“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能火,说明旅游成了纯粹的自我需求——去博物馆是为了丰富自我,购买文创产品,满足好奇心与探索欲,“我想游就游”。人们的主观意愿成了第一驱动力。
在我看来,未来的旅游会更加“无理由化”。就像海子写的诗“人活在世上,总要看看太阳”。当旅游彻底摆脱功利性目的(比如学习、社交),变成和吃饭喝水一样的生命需求,这才是观念真正的解放。现在年轻人中说走就走的旅行、环球旅居,都是这种观念的雏形。
读+:您提出,旅游从来不缺文化,特别是中国,我们有的是文化,但缺的是灵魂。这里的灵魂指的是什么?旅游的灵魂是可以设计出来的吗?
沈祖祥:很多人一听到“灵魂”就觉得玄乎,甚至避而不谈,但旅游景点如果只有文化堆砌,没有灵魂,就像一个人“五官端正却气质全无”。打个比方,文化是食材,灵魂就是菜谱。我们缺的不是食材,而是怎么烹饪这些食材。
我们常常看到现在古镇遍地都是明清建筑、非遗小吃,文化元素堆得够足吧?但为啥好多都倒闭了?因为缺了“灵魂”这股精气神。旅游地空有文化却没“魂”,就成了流水线产品。
我想强调的是,文化不等于灵魂。现在全国各地的景区都在“挖名人、仿造古景观”,以为有文化就等于有旅游吸引力,然而严重雷同的风格只会让一个景区变得毫无魅力。我认为一个项目能不能成功,跳出文化很重要,作为旅游策划者不能总是将文化挂在嘴边,文化不能被人们消费和享受,必将产生冲突。
莫干山一直是德清旅游名片之一,有“江南第一山”美誉,近期,德清莫干山国际旅游度假区要创世界级旅游度假区了。
当年,德清县委托我做《环莫干山乡村旅游带概念规划》。2010年,我提交了规划评审终稿。莫干山是中国四大避暑名山之一,按传统思路只能做“避暑”概念,但我反复思虑,它的避暑名气超不过庐山、承德。既然“避暑”拼不过别人,那就不做“山”的文章,改做“人”的文章。
我当时就想:德清能不能换个“魂”?我找到了一位历史名人,孟郊。孟郊是德清人,德清现在仍旧保存着孟郊祠。孟郊虽然不如李白有名,但他的《游子吟》人人会背。有朋友建议紧抓“孝文化”“母爱”这些概念,我偏偏抓住“游子”的心理——现代人不也像游子一样在城市漂泊吗?于是,我把“游子心绪”抽出来,打造“中华游子文化节”。
另外,莫干山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洋家乐”策划也较为成功——这里吸引了许多外国人租借当地乡村的民居,改造成休闲住宿场所,吸引了大批户外运动爱好者和向往健康生活的白领、外国游客,由此诞生了一种由国际文化与中国乡村文化紧密融合的乡村旅游新业态。现在莫干山成了网红民宿胜地,靠的不是避暑,而是依托“都市人心灵栖息地”这个设计,打造出松弛美好的度假氛围。
“设计灵魂”不是拍脑袋编故事,得有三个支点:挖文化里最戳心的点、抓住当代人的情绪需求、落地方案要具体可感。打个比方,就像捏泥人,文化是泥巴,灵魂是你要捏成杯子还是花瓶,设计就是那个成型的过程。
■ 现代旅游故事本质是策划者与游客的共同创作
读+:有句话是“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万里挑一的旅游灵魂可以设计,是否会陷入同质化的套路中?
沈祖祥:这事儿得从根上捋。好多人担心方法论就是套路,其实恰恰相反,没方法论才会同质化。我总结旅游灵魂设计有“三步法”,每一步都可以避免景区“撞脸”。
第一步是“找魂”,不是随便抓个文化元素就当魂,得像捞碎片似的解码本地基因。比如描述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海派文化、江南底蕴都是原料,但灵魂还得是“魔都”这个能戳中它混搭气质的词;山东以前的旅游口号是“一山一水一圣人”,比较生硬,后来提炼出“好客山东”,把文化变成了能互动的情绪,这就是从“堆料”到“找魂”的区别。
第二步是“造魂”,得在基因基础上搞创作。拿我参与策划山东邹平的项目举例,邹平是范公故里,但仅仅突出范仲淹故居是难以有长久的吸引力的,抓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再结合当地乡村特色,我们把“魂”做成“忧乐精神+乡村实践”的混搭,与游客的心灵共鸣就营造出来了。四川江油是李白故里,我们不硬蹭李白生平故事,而是从孩子都会吟诵的《静夜思》里打捞“月亮”元素,策划中秋诗会、建“诗仙问道”主题区,从文化符号里凝练出独特情绪。
第三步是“销魂”,是靠营销把魂传开。位于浙江的安吉、德清、长兴都是竹乡,如何差异化竞争呢?安吉有“黄浦江源头”的地理标签,另外,“安吉”这两个字寓意着“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把“源头”和“吉祥”捏合成“山水源头+祈福文化”;德清做“游子心”,刚才已经提及;长兴做“茶禅”之味,因为当地有唐代茶圣陆羽遗迹,又有佛教寺庙。我们策划时把“竹”和“禅”结合,营造“竹茶禅修之旅”,游客到访此地,能学做竹制茶器、体验禅茶仪式,体会竹里藏禅意。这样一来,长兴的安宁和安吉的热闹、德清的乡愁就拉开了差距。
打造好的旅游目的地不是盯着老祖宗留下的硬件不放,营销一堆雷同的故居、祠堂。我们得在文化里找打动人心的点,那才是戳中当下人心理的关键。
读+:这对旅游策划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才能发现这些独特而精准的点呢?
沈祖祥:学习很重要,了解在地文化很重要,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认知问题。最基本的认知是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发展、现在与未来。我认为旅游策划师是需要视野和智慧的,还要具有强烈的市场感。策划者为旅游设计“灵魂”,要对历史负责任、对未来有价值。
首先,列清单是个不错的方法,把所有线索摊开晒。比如做一个古镇项目,线索可能有:历史遗留古建筑、非遗手工艺、本地小吃、名人故居等,通过筛选找到最合适的方案列表。筛线索就像揉面,得反复摔打才能出筋。其次是要做减法,这需要一些哲学思维,可比喻为哲学中的“道”。今天各县、各市的项目已经不少了,《老子》中提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然而最终要做的是如何在“万物中找到一二三”。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打造最佳旅游目的地。提到阳澄湖,人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去吃大闸蟹;提到普陀山,人们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去许愿还愿——高度概括,回归本源,我们要找到的就是这样的核心。
读+:做旅游必须考虑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综合效益。从“流量经济”到“留量经济”,关键点是什么?
沈祖祥:这事儿可不是“鱼和熊掌”二选一。现在不少误区就是把流量和长期发展当成对立面。
我们当时设计宁波梁祝文化公园的时候,也是费了不少脑筋。大家都知道梁祝的故事是悲剧,讲起来总是有些悲情色彩的,游客来了一次,若是没有愉悦的体验感,是难以来第二次的。反复设计推敲后,我们抓住“忠贞不渝的爱情”这个关键点,把讲述故事的角度向“爱情信仰”这个方向扭转,设计了一个口号,挺有意思的,“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同样是梁祝故事,有了灵魂引领,就从一次性打卡地变成了情侣必去的“爱情朝圣地”,这就是流量和长期主义的结合——把经典故事变成能生长的IP。
对一个旅游目的地精准定位,深挖其文化基因,是策划的关键。咱们的国产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叫好又叫座,正是因为它没停留在“闹海”的老故事里,而是抓住了“打破偏见”这个现代灵魂,这就是主题的升级。
我们要注重游客体验的共生性,现代旅游故事本质是策划者与游客的共同创作。好多地方搞网红打卡点,今天学别人建玻璃栈道,明天抄人家搞灯光秀,短期流量的确挺猛,但往往半年后就没人去了。好的故事是会随着时代而生长的。旅游故事不是凝固的标本,而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每个时代都会在原有故事基础上沉淀新的文化层,形成“历史基因+当代表达”的复合叙事结构,同一空间载体会因时代价值观变迁而衍生新意义。在社交媒体时代,游客的二次传播、打卡行为本身就成为旅行故事的新章节,形成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的生态循环。
这要求旅游策划者具备更强的能力:既要深挖历史基因的永恒性,又要敏锐捕捉时代情绪的流动性,通过持续的故事迭代保持旅游目的地的生命活力。
■ 让游客觉得“这里懂我”“我因这里而不同”
读+:说到底,“旅游终将回归人文主义”。在文旅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策划者应如何构建“以人为本”的价值坐标系?
沈祖祥:旅游策划要构建以人为本的价值坐标,核心是将“人”作为旅游规划与体验设计的原点,打破传统以资源、效益为中心的策划逻辑,建立一套以人的需求、情感、成长为衡量标准的价值体系。我在《我为旅游设计灵魂——文旅策划成功的秘密》《旅游心理学》等书中也写道:必须确立“旅游,人是主语”的共识。
游客需要什么?不是打卡式地到此一游,而是能唤起情感共鸣的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共创者”。不是喊口号式的“人性化”,比如景区标注“亲子友好”,却只有几处儿童滑梯,缺乏父母参与的互动设计,这是浮于表面的工作。传统旅游策划常陷入资源导向误区,比如围绕山水景观建景点、围绕历史文化摆展品,本质是“让人流向物”,而“以人为本”则是反向思考。
说到这里,我想到日本一个可爱的卡通形象熊本熊,估计很多年轻人都很熟悉。熊本熊的故乡熊本县三面环山,有着独特的火山地貌,63%的土地由森林覆盖,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农业县,盛产草莓、西瓜、番茄等各类农作物。
在熊本熊IP形象诞生之前,熊本县只是九州岛中西部海岸线上的一个小县城,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整体经济相对落后。2010年,正值日本新干线全线开通之际,熊本县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当地决定加强城市推广,他们提出了一个靠虚拟明星带活地方经济的战略创意。此重任被交予知名剧作家小山熏堂,他邀请好友、著名设计师水野学一同加入,考虑到日本人对吉祥物有难以割舍的情结,经过讨论,他们决定设计出一款属于熊本县的吉祥物。
这个创意很快落地,熊本熊仅在出道的头几年(2011年至2013年),就给原本默默无闻的熊本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成了顶级IP。
熊本县原本存在感较弱,但抓住“快乐治愈”这个现代人刚需。用文化符号建立情感连接,用事件营销制造传播裂变,用政府资源保驾护航,用事件营销激活传播裂变,借多方合作实现资源增值。这种“小成本撬动大流量”的模式,是值得研究的文旅策划范本。
简言之,“以人为本的价值坐标”不是让旅游迎合人,而是通过策划让人与目的地产生深度羁绊,让游客觉得“这里懂我”“我因这里而不同”。
读+:作为文旅专家,您对武汉的文旅发展有怎样的评价?结合城市特色,您对武汉文旅发展有哪些建议?
沈祖祥:我对武汉文旅的评价是八个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如果说一定要提一些建议的话,我有这样几个想法。武汉文旅的发展既需要顶层设计的高度,也需要特色凝练的温度,更离不开创新突破的锐度。
一是进一步提升文旅地位,加强对其重视程度。必须把文旅发展放到城市战略的C位,把“长江文明枢纽城市”的金字招牌立起来。提升文旅投资比例,让两江四岸、历史街区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
二是用心深挖武汉文旅的特色,让“江湖之味”成为核心竞争力。盘龙城的厚重、老汉口的烟火、光谷的活力,都是独一无二的宝藏,荆楚文化、工业遗产、红色记忆的潜力巨大。
三是想方设法助力武汉文旅的出新出彩。创新是文旅出圈的关键。武汉蕴藏着许多新玩法,营销上更要大胆破圈,以科技赋能,让世界看到武汉的多样魅力。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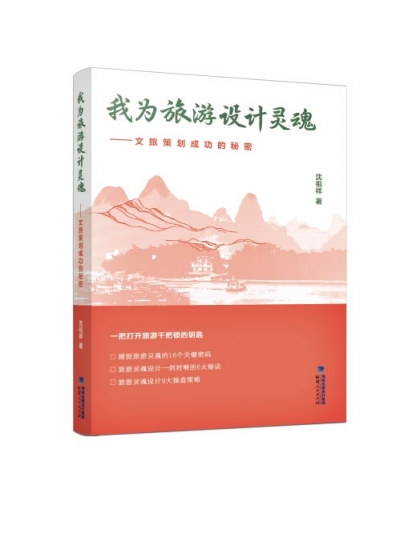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