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其建设质量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城市的整体形象。近日,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专业总工程师钟律出版著作《好社区:人民城市的微观尺度》,书中对一些社区治理优秀案例进行了总结,对人民城市建设理念进行探索。钟律从微观尺度出发,深入剖析了社区建设的多个维度,为行业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上周,《读+》周刊专访钟律,她指出,好社区的规划要关注人的尺度、街道的宽度、邻里的互动等。一个好的城市形态不由大楼的高度决定,而是由公共空间的质量和人们的幸福感决定,微观尺度的设计决定了日常生活的舒适度。“在人民城市中,每个社区都应当是生活的舞台。”好社区的打造不是简单“给空间”,而是要“培育主人”。未来社区的灵魂得让居民自己来塑造,设计师的任务是搭建舞台,要把话语权和创作权交给居民自己。
■ 淡水路,可以很浓
钟律关于社区的记忆,始于上海梧桐区的老洋房。上海梧桐区是上海中心城区优秀历史建筑最多、历史风貌格局最完整的历史文化风貌区,这里曾是租界区,藏着上海自开埠以来的半部历史。
钟律一家三代人曾居住在陕西南路13号。钟律的外公是中国著名规划专家吕光祺。1951年,吕光祺先生跟随建筑大师汪定曾先生,作为核心设计者之—,参与了上海曹杨新村的建设,使其成为全国第—个专为工人建造的现代化家园。此外,他还主持了1986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即使到了晚年,他对城市发展的深入思考也从未停歇,经常伏案疾书,手稿堆积如山。
那时候的钟律还不能完全读懂外公规划图纸上的线条,她最爱做的事,就是趴在窗户看外面的风景。
对面的马勒别墅像童话里的城堡,梧桐树下有人骑自行车慢悠悠地经过,夏日骤雨打在柏油马路上,环卫工人扫落叶的唰唰声总在清晨响起……社区灵气十足,“你能清晰地感受整个街区的节奏”。
后来,她家搬到了虹桥新村。钟律一家所在的这栋楼里,楼上楼下住着长辈的同事。“但我们彼此之间来往得不多,大家似乎都在相同的平面格子里过着不同的生活。”
再后来,她搬入商品房,又过了段时间,她搬家到了远离市中心的郊区。居住的私密性越来越好了,但邻里间的交流越来越少了。
有时钟律回到小时候住过的陕西南路看看,以前的老房子变成了一间酒吧,以前的街道成了网红打卡地。她坐在酒吧里,思绪常常跳脱音乐之外,想起童年时那些自行车铃声、扫落叶的簌簌声,还有邻里之间的问候声。
现在,钟律大部分时候住在母亲的公寓里,和社区的邻居们关系融洽。微信群里的互助信息、放在门口的蔬菜、深夜帮忙取药的邻居……她愈发觉得,社区的温度不在于建筑的外表,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链接。
受到外公的影响,钟律选择了景观设计专业,希望能把艺术的感性融入对“人与场所关系”的理性思考中。她尝试将艺术感知融入街区更新,把它们变成人们可以漫步、停留、感受生活的城市剧场。在外滩,钟律参与设计的景观让游客能沿着江边散步,欣赏历史建筑和现代都市的完美融合;在梧桐区,她用艺术手法改造街边空间,让咖啡馆的外摆区域成为邻里交流、游客歇脚的互动角落。
好的设计应当让空间成为情感的容器,而不仅仅是混凝土的堆砌。
钟律带领团队设计淡水路完整社区,巧妙地用“浓生活”的主题来对应淡水路的路名。这里叫作淡水路,但设计的巧思浸染着浓浓的人情味。街区议事厅永远向市民敞开大门,重视他们的需求;共享自习室提供给年轻人奋斗的空间,咖啡香弥漫,价格亲民,味道也不错;书香漂流站里总有好书在传递;母婴室、适儿化改造过街设施、无动力体育设施,照顾妇女儿童所需……浓浓邻里情在这里蔓延,设计终归是要熨帖人心。
淡水路完整社区的街头有一句标语:淡水路,可以很浓。这是钟律做社区规划设计最理想的境界:细微之处,凝聚浓浓人情。
【访谈】
■ 以人民城市的微观尺度丈量幸福感
读+:您以“人民城市的微观尺度”为角度来写社区,有怎样的考量和想法?
钟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提出建设文明城市需要打造“四个好”,即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这一理念遵循从微观到宏观的逻辑。城市是由一个个微小单元构成,好房子作为基础,是构建理想城市空间的起点。
微观尺度,指的是深入社区内部、聚焦居民生活细节与需求的一种社区建设视角,将社区视为城市的基础细胞,突破宏观城市规划视角,专注于社区这一相对较小范围的建设与治理。我们更加关注社区公共细节空间,强调居民的行为与需求,融入人文关怀与文化元素。
以黄浦区为例。上海是“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首提地,黄浦区作为上海核心区域,土地资源极为稀缺,我们在推进“15分钟生活圈”建设时,无法采用理想化的模式。为此,我们采取整合资源、见缝插针、置换空间内容等策略,根据不同区域特点一案一策,避免“一刀切”。在具体实践中,社区的更新改造涵盖多个方面,不仅包括老城区旧房子改造、公共地块与公共房子改造,更是打造了许多温暖的空间。
以徐汇区的“精细化街区”来说,设施区和通行区是划分开来的,人们可以骑车慢行,在口袋公园徜徉;无障碍通道照顾到老人妇女儿童以及残障人士,还有老幼专门行走的路线;在这里,商店招牌的灯光都是背发光的,柔和自然。社区里还有个有趣的“生活盒子”,集中展示社区里的各种信息和资源,比如社区新闻、工作招聘、公益课堂等,生活在社区里的人是“温馨的一大家子”。
相对于传统的刚性设计,这样的柔性设计更强调无界的包容,融合街道的物理与精神边界。更强调公正与资源共享,以适应不同年龄、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的使用者的需求,为全体城市居民打造无界的社区服务圈。我认为,以上理念便是城市设计中的“温度设计”。
好社区的规划要关注人的尺度、街道的宽度、邻里的互动等,微观尺度的设计决定了日常生活的舒适度。
读+:好社区的“好”经历了哪些变化?在您看来,现在人们对于好社区的标准是怎样的?
钟律:早期社区建设以“解决居住刚需”为核心,关注住房面积、基础设施等硬件指标;如今,社区功能向“复合化”转型,不仅完善养老、托育、便民商业等基础配套,还通过“15分钟生活圈”整合医疗、教育、文化等资源,实现“居住+服务+社交”的多元功能融合。
传统社区规划更注重建筑布局、交通流线等空间形态,当下则转向“以人为主”的体验设计,空间与居民日常行为(散步、社交、遛娃)深度绑定。
早期社区更新侧重建筑修缮、环境美化等物质层面,现在更注重文化内核的传承。
总的来说,好社区的选择本质上是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选择背后是人们对物质需求、城市认知、精神追求以及个人世界观的改变,这些改变也在不断重塑着人们对好社区的理解。本质上,好社区已从“物质指标”升维至“人的体验”,不仅是建筑与设施的集合,更是让居民感受到“被看见、被尊重、被需要”的生活共同体。
读+:人们塑造了社区,社区也塑造了我们。在您看来,社区营造的氛围对我们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
钟律:社区人是生活在同一区域内、具有共同利益并在生活上相互关联的社会群体,是宏观社会的具体表现。对待社区空间环境的态度映照出社会对环境的态度和价值观,社区是人们为自己选择的小世界,社区也意味着人们与居住环境之间的一种有意义的关系。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而这部历史总是与生活的空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与具体的街道和房屋的空间形象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有儿时的梦想、成年时的记忆,人们所居住和工作的街区、学校、广场、花园,每一条街巷、每一片弄堂、每一处建筑、每一株树木、每一块砖石,无不记述着人们的历史和文化。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社区,指的是生活圈社区,也就是居住社区。现在所提倡的“完整社区”,包括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健全、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活动空间充足、物业管理全覆盖以及社区管理机制健全等目标。社区是多元的、异质的、丰富多彩的,而好社区则有许多共同点。
好社区是人们追求和谐共生的理想图景,它既是内心对归属感、安全感与相互尊重的追求,又是对外在环境美好、有序与持续发展愿景的映照。
好社区不仅提供了物质得以存在的空间,更是精神向往的港湾,它是个体与集体、自我与他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微观宇宙。好社区的意义不仅在于物质条件的充裕与完善,更在于精神价值和文化内涵的丰富。
■ 好社区尊重情感、包容需求
读+:中国正面临着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少子老龄化趋势明显。在社区建设中,如何兼顾老年人、青年人和儿童等全龄人群的幸福需求?
钟律:在社区建设中兼顾全龄人群的幸福需求,需从空间设计、服务供给与社群互动三个维度入手,以“人性化细节”与“多元化场景”实现平衡。
对于老年人,核心是解决“行动便利”与“情感陪伴”的需求。例如在空间改造上,加装电梯,配套社区花园的“阳光休憩区”,确保老人下楼后能通过无障碍通道到达活动场地。我们做淡水路社区改造时发现,老年人占比近40%。针对老人的生活照料,社区里设立老年食堂并发放餐券。食堂的饭菜价格不贵,都是老人喜欢的“带锅气”的清淡美食。在石库门弄堂等老旧社区,我们布局定点助浴站,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上门协助洗浴服务。我们为一楼老人打造“轮椅友好型花园”,将浇花水龙头高度调整至适合轮椅操作的位置。
年轻人更需要“社交空间”与“发展机会”的融合。社区可开辟“共享厨房”“书香咖啡厅”等平价社交场所,引入残障人士制作咖啡的公益模式,既创造就业机会,又营造轻松的社交氛围。我们还组织了“素人技能分享会”等活动,为年轻人提供展示专业背景的平台,让社区成为职场之外的“心灵缓冲带”。在淡水路345弄,葡萄架下摆放好茶桌椅,人们可以在这里“围炉茶话”,聊天交友,非常惬意。
孩子们在辖区里也得到充分的尊重。在淮海中路街道“一街一路”项目里,我们以儿童的视角建设好社区,邀请画家开设亲子绘画课堂;带孩子们进行职业体验,了解安全科普知识,让孩子们担任小小街区治理员。
好社区里的书香氛围必不可少:“家+书屋”是好社区读书会推出的多期活动,书店、高校、图书馆、各类文化场馆及线上平台都参与其中,居民获得知识的方式更便捷了。
社区需打破群体壁垒,构建跨年龄的互助网络。在黄浦区淡水路244号,有一处特别的知识共享空间——好社区读书会。通过盘活闲置空间,我们打造出一个集阅读、交流、艺术创作和社区服务于一体的多功能空间,通过读书会、健康讲座(如女性甲状腺知识科普)等活动,让不同职业、年龄的居民共享资源,使“健康、衣食住行”等服务融入日常,最终形成兼具凝聚力与包容性的生活共同体。
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以地域文化为根基,因地制宜整合资源,让每个群体都能在社区中找到“被看见”的需求支点,实现幸福体验的平衡与共生。
读+:在您看来,打造幸福社区的关键点有哪些?
钟律:具有幸福感的设计,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它不只是看着赏心悦目,更要实实在在提升生活质感,体现对人的关怀。
这种设计必须是包容的,要照顾到所有群体的需求。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苏州河边走走,沿着苏州河护栏边,人们可以阅读、触摸到诗歌——静安苏河贯通公共艺术创作团队联合新民晚报社,曾向市民征集诗歌、选出优秀诗篇,以文字、盲文的形式镌刻于河畔的栏杆处,视障人士也触摸到盲文诗句——人民书写的水岸,真切地呈现出城市的浪漫。
具有幸福感的设计得有疗愈作用。徐汇区的西岸自然艺术公园里既有森林、草原、瀑布等自然景观,又有露天剧场、咖啡书吧、滨水舞台等人文风情。孩子们可以在森林里探秘撒野,户外爱好者在这里露营、享受水上项目,文艺青年在这里逛创意市集,在露天剧场里看话剧……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幸福的设计是得有智慧的。设计,必须尊重生活在这里的人,保护他们对家园的那份深情。
20世纪50年代,上海为解决工人住房问题,开启了工人住宅建设工程,计划建造2000个住宅单元,预计可容纳20000个家庭居住,由此得名“二万户”。这些住宅参照苏联集体农庄住宅样式,承载着工人阶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上海长白新村街道228街坊,正是“二万户”工人住宅的典型代表,这里曾坐落着12处联排房屋,建筑密度达32%。早期,众多沪东各厂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在此安家。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房屋逐渐陈旧破败,违章建筑丛生,居住空间日益逼仄。
2016年,228街坊被纳入上海市城市更新项目。228街坊的改造,不仅沿袭12栋风貌建筑组团结构和建筑围绕中心绿地的院落式布局,置入露天电影院、户外儿童足球场、景观廊架、中心舞台等活动场所,还依据建筑空间与功能,设置相应商业外摆,加设座椅、平台、廊架,形成共享休憩的日常交往空间。
设计师保留“二万户”特色住宅原貌的1号楼、8号楼,打造上海工人新村展示馆,作为工人集体文化的活态档案馆,展现了工人阶级生产生活实景与集体记忆图景,将个人记忆升华为社区共同财富。
幸福社区的设计不能高高在上,得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真正的更新,是唤起大家对这片土地的情感,而不是一味地推倒重建。
■ 共建共享,最好的设计专家就是居民
读+:好社区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共同营造的。普通市民如何成为“主动营造者”呢?
钟律:未来社区的灵魂,得让居民自己来塑造。我认为设计师的任务是搭建舞台,话语权和创作权得交给居民自己。最好的设计专家就是社区中的居民。衡量居住得幸不幸福的关键,就是他们的需求能不能被看见,能不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尊重。
在收集居民意见与激活共创积极性方面,要从三方面着手。
首先,构建多元化民主渠道,通过开门纳谏、问卷调查、居民议事厅等形式,保障全过程民主管理,如上海陆家嘴水环(由黄浦江、张家浜和洋泾港构成,和陆家嘴滨江区域形成“O”字形的水环,旨在打造多元开放、活力有趣、人文生态、便捷友好的滨水空间)项目,就是通过了多场沟通会,协调央企国企及多街道,解决工地共享、地块开放等问题,实现公共空间贯通。陆家嘴水环的景点命名,充分吸纳居民基于在地文化记忆提出的建议,让居民的点子在项目中得到展示。
其次,注重居民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将专业设计转化为简单易懂的问题清单,围绕衣食住行、邻里关系等居民切身需求设计问卷,让居民通过勾选表达意见,完成用户画像。
最后,要将项目成果与居民创意结合。这一过程中也许会存在专业表述与居民理解之间的沟通难题,但通过需求转化、清单化提问等方式,有效化解矛盾,推动居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才能真正实现社区共建共享。
好社区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它要求我们深刻理解合作与共享的重要性。从好房子扩展到好社区,以及整个好城区,居民每一分参与都能让幸福感更多一点。
城市属于人民,建设必须回归“人”的价值本位,将市民需求作为规划起点和落脚点。人民不仅是城市服务的“接受者”,更是治理的“参与者”、发展的“共创者”。
读+:基于好社区的创建模式,您能否总结经验,给予具体的建议?
钟律:在上海好社区营造的实践中,我们总结出几点可借鉴的经验。
首先,要打通政策壁垒。负责社区建设的部门可能包括街道、住建委、职能部门等。不同职能部门职责不同,需要打开每个部门之间的政策壁垒,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百姓服务。
其次,要注重普惠性与公平性,不能只盯着历史保护区或网红地标,更要聚焦普通新村这类大量存在的居住空间,让更多居民受益。
另外,需要通过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共建来缓解资金压力。政府可能会搭建平台,让更多新技术形成产业链。当我们将部分基础设施和城市修缮资金提供给产业链时,产业链会更加健康地成长,同时反哺居住环境的更新。
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中国特色幸福社区的打造关键在于“共同创造”,不是为了故事而打造,而是从居民真实生活需求出发,让大家主动参与进来,这样才能真正营造出有温度、可持续的幸福社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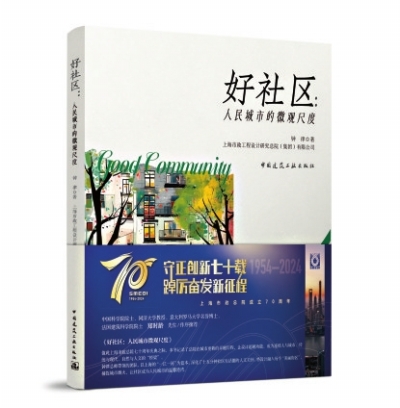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