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燕鸣
2021年初冬,我决定去一趟久违的汉正街。或因那篇写了3万多字的故事一直停滞不前,想寻找一下灵感和素材。
曾几何时,我与大多数人一样,对汉正街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曾号称天下第一街,是全国首个小商品批发市场,一个又一个的商业传奇不断上演,名噪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汉正街》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商人们的故事。而我也在其高光时刻的20世纪90年代初,实打实地在此居住过几年,当时的家就在花翎巷里,从朝南的阳台越过层层叠叠的屋瓦,就能看到悠悠的汉水。我深深感受过汉正街的嘈杂和喧闹,狭长的石板路上,每天挤满了南来北往的打货人,他们在堆满五花八门小商品的店铺里与老板讨价还价,然后用蛇皮袋或大塑料袋子装好货物,或肩挑背扛,或用板车、三轮车推着,在摩肩接踵的石板路上缓慢前行,时常因来往的车辆阻碍,被挤得动不了……这样的情景,我曾在长篇小说《汉口之春》与中篇小说《小巷里的女人》中有所描述,那种热腾腾的人间烟火,醇厚而深长,一直留在记忆中,挥之不去。
然而,当我再次走进汉正街时,已是另一番面貌,曾经热闹拥挤的狭长老街已不见了踪影,道路都扩展了,高楼大厦取代了高低错落的老房子,充满了时尚气息,商铺也都搬进了楼内,成为商城。我独自走在高楼林立的大街上,恍若隔世。一直到大夹街深处的药帮巷,才找到一些旧时的痕迹,那条硕果仅存的青石板路,蜿蜒百米长,两旁依旧是老房子,市二色织布厂的四层白楼所幸还在,我在那门前站了好一会,回想曾外祖父、外祖父曾从这里进进出出,不免思绪万千。
不知不觉间,脚下的青石板路在延伸,狭长的正街望不到头,店铺招牌密密匝匝,烟气袅袅,人声喧阗,我穿行在人流中,又进入了当初的情景,也似乎坠入了前世。
突如其来的创作灵感也在那一瞬电石火花般闪现。然而,祖辈在此耕耘的情景于我还是陌生的,这不禁激起我探寻的欲望,但查找的资料和一些文学作品多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汉正街,此前的内容寥寥无几,唯有清代竹枝词记录一些曾经的景象。但药帮巷让我的思绪得以拓展,我想跳出80年代的模板,向更悠远的岁月回望。
这自然是了解历史后的拓宽。都知道武汉分三镇,从隋代这里就形成汉阳、武昌“双城夹江”的格局。自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将汉阳一分为二,劈出一个水汪汪的汉口,随后各处商民渐渐在水口两岸建房造屋,商船来此停泊,从满滩芦花、鱼跃鸢飞的泽国迅速发展崛起。从明嘉靖到清嘉庆二百余年间,汉口从一个荒洲跃升为全国四大名镇之首,为“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的“楚中第一繁盛处”。汉口因河而兴,因商而活,“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写的就是当时汉口口岸(汉正街一带)的繁荣景象。汉正街是汉口之正街,也是设立许多地方官署的官街,汉正街是汉口商脉,是汉口的城市之根。尤其是汉口开埠之后,武汉联系了广阔的外部世界,随着西风东渐,洋务运动在武汉应运而生,自此,武汉城市才真正步入近代,才有了城市性质和社会的转型,使汉口由封闭型的封建商镇,演变为开放型的具有一定近代文明的大都会。但历次的战争,汉正街与汉口城市一样,屡遭重创,也总能浴火重生。到了20世纪20年代,汉口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长江航运和京汉铁路两擎并驱,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
于是,我又开始续写那部停滞不前的小说,将女主人公暹春出生的丁卯年(兔年)作为小说的起始,也正是不同寻常的1927年,北伐军在武汉建立了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虽只有短暂的几个月,但对武汉影响深远。也是这一年,三镇才正式有了武汉市的命名。
我时常去汉正街的街巷里穿行,也去汉阳洗马长街附近寻访,捕捉那些旧时的味道,如果遇上一两位老街坊,如见故人,会慢慢地倾听对方讲述曾经的往事,日光悄然无声在斑驳墙面上移动,将所有沧桑变成金色质地的风物,那些往事也成为小说里的情景。我的脚印也变为主人公暹春的足迹,在蜿蜒曲折的石板路上延展着,如同她颠沛流离的命运,从汉正街到洗马长街,她眼里的情景渐渐变成了长长的画卷,逶迤如一条无尽的长河。
有时我想,武汉究竟是座怎样的城市,能驱使自己一次一次地抒写,说不完,道不尽。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触摸历史的过程,逐渐发现这座城市的厚重和底蕴,武汉从1986年就被国务院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真不是浪得虚名。如果一座城市让人一目了然,让今天的人感受不到更多的历史传承,无疑是可悲的。武汉确是一座一言难尽的城市,她的人文历史,她的得天独厚,她由大江大河滋养的风情和性格,由此呈现出今天不一样的魅力和特征。
甲辰年的阳春三月,我已完成了长篇小说《暹春纪》,特地去汉阳龟山浏览,因汉阳的洗马长街也是小说的重要背景,我在小说里对清初名士毛会建先生也有所描述,就想去寻其遗迹。毛会建先生在学林被誉为“书法逼晋魏,六书篆皆精绝”的金石书法家,其书法苍劲,类颜鲁公。毛会建也是位探险家。嗜奇癖古,游迹几周天下。他曾到衡山岣嵝峰历经千辛万苦寻得世间珍品大禹碑,并勾填后摹刻在龟山。毛先生晚年居住汉阳晴川,曾在龟山周边遍植树木,相传汉阳禹碑亭东面一棵巨大的古椿树就是他栽种的。我在《暹春纪》中,也收入了毛先生的《晴川朴树》诗。他在《晴川补树》诗自跋中曾写道:
自崔左司(崔颢)《黄鹤楼》诗而晴川以树闻,历千百年以至今,何濯濯也。予乞诸万木园,得榆、柳、柏数种补之,清川绿树,一时掩映,倘亦好事者之所为欤?
崔颢的一首《黄鹤楼》让晴川树名满天下,然千百年后,龟山已濯濯然也,所以毛先生补种树木,力求千百年后绿树成荫,枝干交错,再现“晴川历历汉阳树”的风貌。
如今的龟山已是层林叠翠,我在花红绿柳中漫步,想毛先生安眠在这片茂密丛林中,也会含笑九泉了。然而我却没找到毛先生的墓碑,唯有曾立于蛇山抱膝亭前的黄兴铜像转移于此。漫步下山来到对面的晴川阁里,凭栏眺望,蓝天白云下,一条大江闪着金光汩汩流淌,静静穿过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不觉庆幸将建设长江大桥的情景做了《暹春纪》的小说情节。
晴川阁大殿里,中央挂匾的“山高水长”四个遒劲大字,正是毛会建先生所书,两旁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晴川阁所撰楹联“洪水龙蛇循轨道,青春鹦鹉起楼台”,由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社长沙孟海先生书写。
流连之间,发现晴川阁外也树有一块“山高水长”的石碑,与大殿内的四字相同,皆从西安碑林的原碑拓印而来。走近一看,上款题写:康熙甲辰行醉日。我盯着甲辰二字,一时惊住,怎就这么巧,竟也是甲辰。蓦然发觉,把毛会建写进小说里,也像有只手在指引着我。一些人物的出现,也并非我刻意而为,至小说完成之后,才知道是带着使命而来。
乙巳年的阳春三月,我重游西安碑林,特地去寻找毛会建所书“山高水长”的原碑,抚摸着那碑上精雕细刻的字迹,禁不住泪眼婆娑。耳边似有人在吟诵着:“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是晴川绿阴下借酒挥毫的毛会建,还是受先生之风浸润的暹春,抑或是不断进取的每一位武汉人,皆聚成那座英雄辈出的城市,岁月更替,风华依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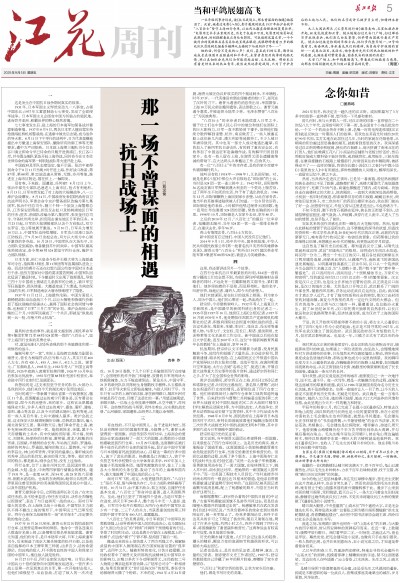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