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波
近来,有朋友打算利用参加第二届楚文化节活动的机会,到我的家乡荆州古城游玩几日,问我要一份攻略。我笑道,网上啥都有啊。朋友却振振有词地说,旅游问土著,避免走弯路。说笑间,“土著”两个字一下子牵动了我的神经。
从籍贯来说,我确实是荆州人。我出生在荆州区一个农村,小学时随父母举家进城,寄居在姨父一家经营的一个木材厂,位于荆州区主城区之外。一直到我高中毕业,在古城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珍贵的求学时光。
想到这,我告诉朋友,怕是做不出攻略来。朋友不可思议,还有人对家乡不了解的!我解释说,吃喝玩乐、风土人情,上网能查,不必赘述。我倒是曾经在这座古城上学九年有余。没承想,朋友一下子来了兴趣,上学趣事才多,快说道说道。我顿了顿说,那就先说说“古城”之称。
荆州作为城市名称,可追溯至《尚书·禹贡》记载,“荆及衡阳惟荆州”,为古九州之一;以原境内蜿蜒高耸的荆山而得名。据史料记载,荆州古称江陵、郢都、南郡,荆州之名源于荆,是古代楚国的别称,因楚曾建国于荆山,故荆、楚通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在此建都400余年,被誉为楚文化发祥地。现在,人们之所以把荆州称作“古城”,主要因其拥有两千多年延续使用的古城墙建筑体,是考古已发现我国唯一一座连续使用时间长、保存较完整的砖城。按照地理方位,荆州古城墙大致分为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四个城门。其中,南门分老南门、新南门,北门有大北门、小北门、新北门。在我青少年求学的日子里,走过最多的地方当属三个“北门”。
上小学时,我赶早就要从新北门外的住所出发,沿着笔直且不算宽阔的马路一路向西。走到大北门时,我开始兴奋起来,因为路程过半,更因为“大北门”附近会与许多同学相遇,不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一开始,我跟大家一样老老实实沿着马路走,熟悉路况后,放学途中一到此处十字路口,禁不住“诱惑”会中途变道。要么,跟几个同学拐弯朝着城墙奔去,顺着青石板路一路狂奔,跑着跑着到了一条河边,看到河里的小鱼小虾就迈不开腿了,跟着胆子大的同学挽起裤腿摸下河去,忘乎所以地玩到天擦黑儿;要么,几个同学不约而同地在菜市场门口的一片空地集合,打弹珠、玩纸牌卡片、跳橡皮筋,什么流行玩什么,直到家里人叫“回家吃饭了”呼喊声此起彼伏,才意犹未尽地各回各家,并相约明天继续……这些看似“放纵”的行为一直延续到小学毕业。
上初中前的暑假,父母忙于务工,时下热门的毕业游、培训班通通没有。我集中一个星期时间做完暑假作业,便开启了“散养”的假期生活。令父母倍感欣慰的是,我不仅帮忙做家务,而且还能搭把手帮他们做体力活了。
初中位于小北门外比较偏远的郊区,相比位于大北门外的小学,路程更远。一开始,父亲蹬着自行车,早送晚接风雨无阻,但是由于晚上不定时还要干活,导致我经常成为最后一个被接的学生。好几次,班主任处理完琐事出校门时,见我还在大门口苦等,便给家里打电话,陪我一起等家人赶来。
“晚接”太晚了!母亲一方面觉得父亲太辛苦,一方面不忍心我等得辛苦,多方打听淘来一辆自行车,打算让我独自骑车上学,但是又放心不下,便让父亲陪骑。一个星期后,我告诉他们,我记住路了——出家门第一个路口右拐,上大路左拐,到小北门转盘……见我确实对路线滚瓜烂熟,父母最终放手了。这段路从初一开始,一骑就骑到了高中毕业。
巧合的是,以小北门转盘为界,家和学校路程几乎对半。上学时,马路两侧零零散散坐落着几片居民区、几家木材厂、几所学校,临近小北门转盘时变得热闹起来,不仅有闪烁着霓虹灯的理发店、网吧、宾馆,而且有香气四溢的早餐店、熟食店,熙熙攘攘的菜市场。过了转盘,道路两侧开始有单独的非机动车道,且用绿植与宽阔的机动车道隔离开来。每每骑过转盘,我便放飞了,全力加速,把速度骑到最快,享受风呼呼地从脸颊吹过、从耳旁掠过的快感,肆无忌惮地呐喊,尽情释放逐年递增的学习压力,以及青春期潜藏的叛逆。
上高中后,有一阵子每到周六中午放学,我特别不想回家。出了校门,骑车看见路口就拐,也不管到哪里,无头苍蝇式地乱窜,直到无路可走才调头,竟摸索出好几条新路线。有一条路我特别青睐,出校门几十米,从大路拐进仅有一车道宽的水泥路,没几分钟就骑上了不规则的田间土路,不自觉地慢了下来,随兴哼起了那时最爱的周杰伦歌曲《我的地盘》,看着错错落落、一片片青绿色的稻田,闻闻扑鼻而来的油菜花香,转而唱起《七里香》,最后骑过排列整齐但大小不一的鱼塘,那份惬意一直延续到回家做作业。有时候,我飞速骑到小北门转盘,一头扎进开在拐角处的一家书店。门脸儿不大,内里陈设简单,各式各样陈旧的书籍、报刊堆满了角角落落。一进店,翻书、看报、读杂志,站着一直看,看着看着就到了闭店时间。日子久了,店老板认得我了,见我一来,便递给我一张小板凳,让我坐着慢慢看。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我贪婪地看书,疯狂地汲取养分,平静地享受“大快朵颐”的阅读时光。
进入高三,意味着高考开启了倒计时。早晨不到5时,我就得起床赶往学校,晚自习结束回到家已将近深夜11时,学习时间被拉长到了极致,我的神经绷紧到了极致,偏偏同父母的关系也僵到了极致。一向寡言少语的父亲突然提出,每天晨跑送我,晚上到校接我。我一下子莫名觉得,这不就是为了“监视”我嘛。父亲言出必行,第二天一早我背着书包出门时,只见父亲已经准备好跑步出发了。心里有气的我骑在前,只管加速,头也不回。放学后,我推车到校门口,远远地看到父亲扶着自行车,却假装没看见,两脚一蹬骑车飞奔,只想把父亲甩得越远越好。半学期过去,我见父亲风雨无阻,心也软了下来,便同父亲说,您白天干活还需要很大体力,别起早贪黑接送我了。父亲却说,正好锻炼身体,还能陪我聊聊天,一举两得。我想了想说,早晨去时我跑步,您骑车。父亲点头同意。开始的一两个星期,我跑到小北门转盘时,感觉怎么也坚持不下去了。父亲鼓励说,你试着再坚持坚持。父亲一次次鼓励,我一次次坚持,晨跑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这种特殊的陪伴下,我在古城度过了最后一段求学时光。后来,我考上武汉一所大学,毕业后常年在外漂泊,只有休假时才回家与父母待上几日。
听到此,朋友文绉绉地说,古城有“古事”。我感叹道,今时不同往日。脑海中闪过一句古语,“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的求学时代一去不复返,记忆中的几个古城“地标”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慢慢隐退,古城也乘着新时代东风焕发着新活力。而我,一个在古城努力求学、拔节生长,最终离开家乡的荆州伢,辗转广西、云南、北京等多个省市,在而立之年到江城武汉站住脚,正奔跑在新的人生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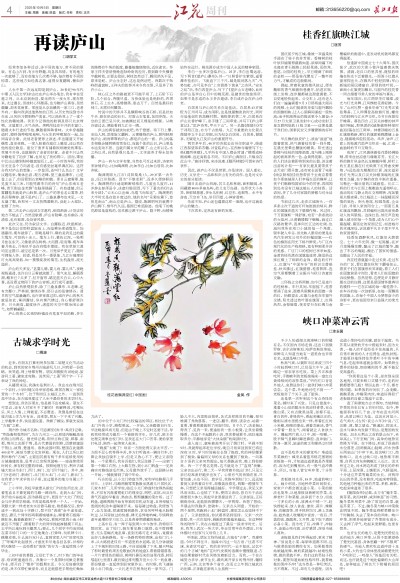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