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聂作平
【编者按】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北方及东部沿海面临战争威胁,数十所大学不得不向西部搬迁,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高校大迁徙。作家聂作平从2016年重走浙江大学西迁路开始,用8年时间实地走访了10所大学的内迁之路,寻访旧址,研究史料,拜访相关人物,写成《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用生动的文笔全面呈现了10所知名大学的内迁往事,并烛照历史背后个人的命运浮沉与时代的峰回路转。本文摘编自该书自序。
■ 从竺可桢的日记开始
我特意查了日记——2016年6月12日,手机响了,央视编导想请我为一部纪录片撰稿,讲述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的故事。
很快,我完成了题为《问天冷暖》的纪录片撰稿,并在央视播出。
纪录片结束了,另一件事情却开始了。
之前,为写这部纪录片,我买回重达二三十斤的《竺可桢全集》,重点阅读他几百万字的日记。竺可桢的日记,显然没打算发表或出版,像鲁迅日记一样,很少抒情、议论,几乎就是每天工作、生活的流水账。这种流水账式的日记,非常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人生历程。
我读得最仔细的,是他在浙大西迁和贵州办学时那几年的经历。阅读期间,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以竺可桢日记为线索,重走浙大西迁路,写一篇关于浙大西迁的长文。
2017年3月11日,我从成都驱车出发。次日清早,我走进了古老的湄潭文庙——它曾是浙大西迁时的校本部驻地,而今改建为浙大西迁陈列馆。
为了获取地方史料,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湄潭县方志办,请工作人员找来县志及文史资料选辑,一一拍照留存。
寻访湄潭4个月后,我再次驱车南下,这一次,目的地是广西宜州——旧名宜山。与春日里细雨濛濛、柳丝轻扬的湄潭相比,宜州的夏天如同一只巨大的蒸笼,潮湿,闷热。这座被戏称为“宜山宜水不宜人”的小城,既是浙大西迁办学点,也是黄庭坚客死地。
宜山时期的浙大校本部,设在宜山文庙——事实上,绝大多数内迁的高校,几乎无一例外地进驻了当地文庙,且大多是校本部。这是因为,作为彼时不多的公共建筑,文庙相对宽阔、齐整。
至于浙大曾经西迁办学的吉安、泰和、金华等地,我之前都去过。
寻访归来,我开始动笔,开始在电脑上敲下第一个汉字。
2017年9月15日,我的长文《苦难催生奇迹:重走浙大西迁路》发表,反响强烈,包括《新华文摘》在内的多家报刊纷纷转载,至于转发的网站和新媒体,更是多不胜数。
媒体的转载和读者的热议,这是一种令作者深受鼓舞的正向反馈。于是,我决定把大学内迁系列继续写下去,写成一部书。
■ 陆续寻访了10所内迁高校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首先内迁。及后数年,从中国北方、东部迁往西南的大学数以十计,从而形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战争中的流亡兴学。
这样的历史,既应该也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我寻访的第二所内迁高校是武汉大学。与浙大辗转迁徙多次不同,武汉大学一步到位,比浙大少受了许多颠沛流离之苦。
在学者孙雁鸣兄陪同下,我攀上乐山老城制高点:老霄顶。站在山上,透过葳蕤的草木,可以看到急流拍岸的大渡河,以及河畔耸立的乐山大佛。当年的老霄顶上,建有武大礼堂。礼堂下方的文庙,是武大总部和主校区。
浙大、武大之后,是华中大学,一所业已不存的高校。它的内迁之地,在桂林和大理——其中,绝大多数时间在大理,在洱海之滨一个叫喜洲的小地方。那也是所有内迁大学中,迁得最遥远、最偏僻的一个。
总之,从2017年开始,此后八年间,为了那些内迁大学,我在各地往返奔波:出发,归来;再出发,再归来……山河万里,风霜以行;岁月往事,中宵跂立。
在三台,秋高气爽,菊花竞放,我和老兄弟田勇登上城外的牛头山,在半山腰,找到了东北大学开凿的防空洞。这座川东北县城最值得骄傲的事,我以为无非两件,一件在唐朝,一件在现代——前者,大诗人杜甫和李商隐分别在此客居;后者,东北大学内迁此地。
在城固古路坝,油菜花开的春日,原野上,花朵像流动的金色颜料。我带着儿子走进山坡上那座悬挂着十字架的教堂,那是西北联大旧址。许多次寻访,我特意带上了儿子。我想让他从小记住,消逝的时光,收纳了这样一些可风可颂、可叹可泣的先人。
从厦门到长汀,暑热的7月,沿途翻越的崇山峻岭,很自然地让我想起当年厦大师生内迁的艰辛。抵达长汀那个夜晚,明月在天,我踩着遍地银光,行走在灯火稀落的小巷。夜深了,月光下,那座写着“国立厦门大学”大字的牌坊,影子斜斜地落在地上。
在北碚,在当地朋友陪同下,我三次寻访位于嘉陵江畔的复旦大学旧址——夏坝,而今,它还保留了当年的地标建筑:登辉堂。登辉堂后面,还有几栋破旧的平房,据说,也是复旦学子的栖身之地。200米开外的大桥下,孙寒冰先生的墓碑上,落着两只小鸟,它们啁啾有声,仿佛在和从桥上飘落的汽笛相呼应。
在澄江、在罗定、在三水、在韶关、在南岭掩藏的诸多小地方,我寻找中山大学的一点一滴。那些遗失在万里山河间的故人故事,只有用细心、虔诚、敬意,才能把它们一一打捞、回收、珍藏。
在上海、在赣州、在贺州、在友谊关、在昆明、在宜良,我打听和同济大学相关的人与事。
我寻访的10所内迁高校中,最后一所是早已拆解的中央大学——它曾是我国规模最大、学生最多、学科最齐全的最高学府。像武大一样,中央大学也是一次性内迁到位的——它从南京溯流而上,落址重庆。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附近的山坡上休息时,我想,我已经寻访了10所内迁高校,可以将这些文章结集为一部书出版了。不过,当年的内迁高校,远不止这些。
我决定:继续走下去。继续寻访。继续书写。
这部书,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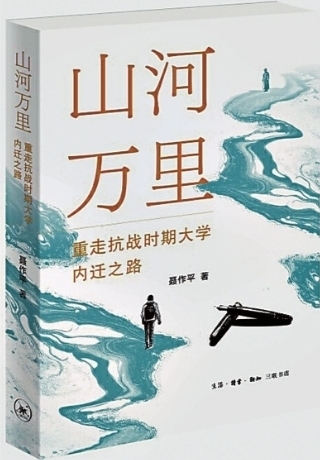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