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飞雁
开封城北东京大道南侧,有个普普通通的村子,名叫“孙李唐”。离村子不远,有家驴肉馆,那日有位当地文友请我喝汤吃肉。文友说,全国有两处地方驴肉做得最好,一处众人皆知在保定,是当时的对辽前线,另一处就在当时的国都开封。原因也很简单,北宋缺马,驴的耐力好、成本低,物资运输以驴为主,军粮不足还能杀了应急,而物资中转地就是开封,食材多了,做得就好。
吃饱喝足,我们在附近闲逛,文友又告诉我,“孙李唐”原本叫“逊李唐”,当年李煜逊位被囚于此,后来南唐遗民多在此聚居,繁衍成村落至今。不经意间的闲聊,不期而遇的收获,都被我写进了小说里。
开封做过国都,做过河南省治、省会,在1954年省会迁郑之前,开封毫无疑问是河南的标签和符号。我在迈出第一步时的初心,就是希望能够重新建立读者对开封乃至河南的文学想象。我写的是一个古代谍战的故事,把我们熟悉的历史和看不见的历史翻转、淘洗,进而重建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学风景。两座开封城都在小说里流动,一个是日常的帝都故事,一个是隐秘的谍战故事,我想让这两个故事水乳交融,在烟火日常中写惊心动魄,在风云莫测中写市井人生。
小说里的“皇城司”,是北宋最为著名和神秘的间谍机构,而与之相对应的辽国“刺机局”,则完全是我的虚构,当然我知道一定会有这样的机构存在,只是被历史中的烟尘遮掩了。《辽尚书左仆射中京留守贾师训墓志》中记载:
“素闻燕京留守府……其府置一局,诸事连外境,情涉谋叛者,悉收付之考劾,苟语一蹉跌,即置之孥戮,亦委是吏主之。”
可惜的是,碑文中我最感兴趣的信息,恰恰是不可考的“一局”。我本想定名为“刺事局”,后来觉得太平常,就定成了“刺机局”。与之相似的还有“皇城司”。关于“皇城司”的史料记载和专门论文极多,但其具体下设机构和行事规则却是语焉不详,我一时兴起,也是行文所迫,虚构了这样一段文字:
皇城司一处四房,素有“劳、险、凶、薄、冤”之称。宫事处守着皇宫禁中,日复一日经年无休,占着“劳”;探事房监察百官动态,侦缉情报间谍,时时命悬一线,占着“险”;刑事房负责缉拿、安保和侦破行动,往往九死一生,占着“凶”;律事房分析情报,保管存档和内部执律,算是“薄”;提牢房则专管关押审讯要犯,刑法惨烈无人不屈,可谓“冤”。
这里的宫事处、探事房、刑事房、律事房和提牢房,以及各自的职责功能,还有“劳、险、凶、薄、冤”的诨名,也是我的虚构。正因为我相信历史中确有其事,我就把虚构也当成了真的去写。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由草动见风姿从而知风”,此谓“假物得姿”。对我而言,从事写作最大的幸福,就是用文学的感官辨识出风的形状。在这部名为《汴京听风录》的小说里,我写的有历史的风,有文学的风,有开封的风,我写的是飞沙,是麦浪,是波纹,是风的姿态。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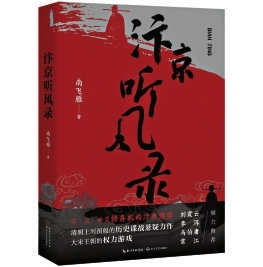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