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明蕾
有心的乐迷应有感知,自年初开始,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尤其C大调第七交响曲已然成为各交响乐团的热门曲目。“肖七”固然是经典,更在于今年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肖七”另有“列宁格勒”之命名,表明作曲家一开始就为这部作品明示了演绎方向。
圣彼得堡爱乐日前再次来到琴台音乐厅,将“肖七”列为重头戏在意料之中。照说该团演绎“肖七”,无论从民族归属、作品所指、文化传统和乐团资质诸方面,都不无优势。该团手上的“肖七”,可谓原汁原味,再地道不过。
如此说来,何不将他们的演绎树为“样板”,各乐团前往“取经”就是,又何必绞尽脑汁地自搞一套,还冒着“不地道”的风险?
音乐演绎变量之多难以胜数,如果克隆“样板”居然成真,那才是一个天大的噩耗降临;可以断定,到那一天,音乐作为“人类精神的火花”(贝多芬语)将就此熄灭。
音乐演绎变量多,多到怎样的程度?感觉上是数不胜数,也有著名钢琴家、上海音乐学院赵晓生教授的文章《音乐的诠释——关于诠释音乐的五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予以理论加持。极简概括赵教授的思想:第一层诠释乃作曲家对自身心灵感受的折射,但写到纸上的乐谱未必与其当初感受一致;第二层诠释是指挥对作曲家音乐文本的解读,由于解读者观察点不同,诠释也每每相异乃至大相径庭;第三层诠释则是演奏者将乐谱转化为音响,这更因演奏者各有理解和风格,现实中的演绎才如万花筒般绚丽多姿、各有面貌;第四层诠释是受众赏乐时的心理反映,100个人心中有100个哈姆雷特,不用多说;最后一层诠释即为音乐学层面的“文字诠释”,读读每场音乐会后的评论吧,哪里有统一的见解。如此每一层诠释都充满变量,再叠加细分起来,变量何其多以至无穷,又谈何“标准”。
所以面对同一部作品,不同的乐团(指挥)自然会“二次创作”出不同的音响;甚至同一部作品由同一个乐团演奏,不同时段都会有变化。正如杜达梅尔携乐团与王羽佳合作时声称:从排练到演出,我们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都在变。音乐是时间的艺术,这也是一种理解。
经典诠释虽无标准,但也不是天马行空,随心所欲,而须“释”之成理,“释”而“靠谱”。所谓“靠谱”,我理解,是经典诠释的说服力。
说到这儿,音乐史上的一个著名桥段就呼之欲出了。话说1962年,古典乐界的两位顶级大咖,美国指挥家伯恩斯坦和加拿大钢琴家古尔德合作演绎勃拉姆斯的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照说勃氏的这一经典为乐界常演曲目,亦为乐迷耳熟能详,两位大咖本应珠联璧合。谁知一向特立独行的古尔德这次却对演奏该协奏曲的速度有了“新发现”,而他所采用的背离常态的理解及诠释,却被伯恩斯坦在开演前公开表明自己生平第一次听到、“某种程度而言是最顽劣的诠释”。虽然指挥家最后向独奏家做了妥协,演出按古尔德的速度进行下去,但伯恩斯坦绝不承认这是他的演绎。
众多音乐家和乐评家卷入了这场由速度问题引起的争论,几乎所有的古尔德传记都从不同角度记载了这一事件。而钢琴家后来对此事来龙去脉的记叙,也让世人得知,古尔德更改速度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有自己的深入研究为据。我们也由此清楚了,所谓“靠谱”的尺度大到怎样的地步。
说到底,经典诠释,“误读”无所不在。可无论是业界还是乐迷,没有谁想到去向某个“正确的样板”看齐。毕竟,多样化是无限丰富的前提,更是一切健康生态的本质,其中自然也包括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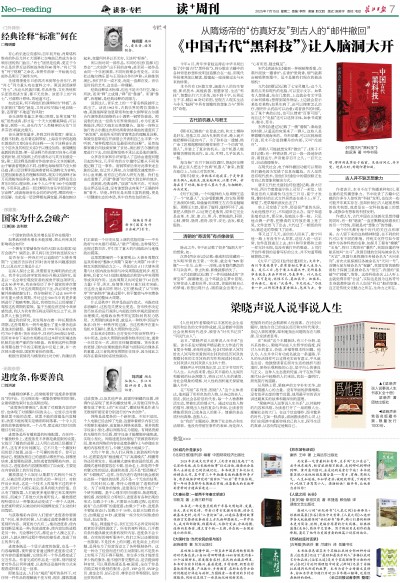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