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茂莉
《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从科普和人文的双重视角穿行于天、地、人之间,展现200多万年间大自然的伟力与沧海桑田之变,回溯华夏文明的起源,感受人类与天、地的关系。从整个地球到中国大地,今天我们周围的一切与200多万年前截然不同,但古今之间却从来没有失去关联,这里包含着大自然的奥秘,也蕴含着人类的奋争。“让历史告诉未来”这一口号,永远不会失去价值。
人类立足于天地之间,从远祖至今,不知经历了多少日月轮回与沧海桑田之变。那是一段漫长的时光,若从东非坦桑尼亚发现的古人类遗骨算起,至少已经有200多万年了。
200多万年内天、地、人并行存在,彼此之间的关系却不同,天、地是大自然的本色,而人类需要仰仗天、地而生存,不仅从中获取资源,也参与了对于环境的改造。
人类参与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绝非有意为之,而是本着求生的本能,但每一项人类活动都成为自然力以外的催化剂,从远古时期在大自然中直接获取动植物资源到农业生产的出现,从工业革命到当代高新技术的应用,人类自身的发展在环境史中不仅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越来越重要。人们在关注自然的同时,也在不断审度自己的行为,并将其注入各类研究中。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人的经济行为开始。在考古学界界定的旧石器时期,人们的维生手段基本是采集渔猎,这是纯粹从自然界索取,因此学术界将这样的维生手段称为利用型经济。距今一万余年以前,人类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尽管这一时期人们手中的工具仍然存在石器,但农业已经出现了。
农业在今天看来属于最普通的经济生活方式,对于那个时代而言却是全新的探索。正因如此,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将这一人类经济行为称为“新石器革命”。显然农业不仅仅是对自然资源的单一索取,而是将人类的生产行为注入其中,并通过人类自身的劳动而产生收获物。因此,学术界将农业称为生产型经济。从利用型经济到生产型经济,人们不仅维生手段发生了变化,而且参与了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这样的改造不仅用农田取代了原生态的地理环境,而且使大自然逐渐失去原有的生物多样性特征。
《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这部著作用不小的篇幅,讲述了在农业背景下人与地的故事,文中的“风吹来的黄土”“寻访桃花源”“天下之中”“大平原”“冲积扇的诱惑”,都没有离开农业,以及人们在从事农业的过程中与大地建立的关系。文中涉及的农耕之地,每一处均非最初就是发展农耕的“理想国”,人们通过农业立足在这些土地上,不仅存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劳动,与之相伴的也是观天时、择地利的改造自然过程。
气候变化是人类始终面对的现象,人类从立足在大地上开始,不仅经历了第四纪冰川以及此后的气温冷暖之变,也在冰期完成了经由白令海峡的迁移。人类是文明的操持者,而对于人类如何产生,即我们是谁、又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问题,无论古今都在思考。《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每个篇章中的“我们”,不仅在思考人之初的那些事,也在人与天、人与地的关系中寻找答案。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整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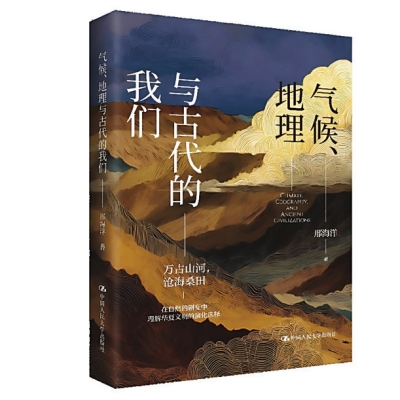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