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洪波
中国古代讲时间的细小片断,或用刹那,或说倏忽。
刹那出自佛教,称一百二十刹那为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为一腊缚,三十腊缚为一须臾,三十须臾为一昼夜。佛教经籍又称“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
这样说,刹那是一个可计算的时值概念。这是佛教可以设想的最小时间单位,确实够短暂,但它没有进行过实际的测量,古代不具备如此精细的计量手段。
放到现在来计量,一刹那约13毫秒,一弹指耗时0.8秒,一次生灭耗时约14微秒。以生活经验看都挺短,但以仪器衡量却算相当长。现代科学计量中,秒以下计时单位有毫秒、微秒、纳秒、皮秒、飞秒、阿秒、仄秒、幺秒,换算关系都是千进制。
倏忽或儵忽出自道家,它不像刹那可以计量,就是指极短的时间。
《庄子》有著名的寓言:儵为南海之帝,忽为北海之地,浑沌为中央之帝。儵与忽时常在浑沌的地界相遇,浑沌招待很好。儵与忽商量报答,说:“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饭、呼吸,浑沌却没有,我们试着为它凿开。”于是每天给浑沌凿开一窍,凿了七天,浑沌就死了。
这里,儵和忽似乎跟时间没什么关系。不过,在诸多古籍中,有“倏忽之间”“倏忽变化”“儵忽往来”“视儵忽而无见”“机变儵忽”等用法,都是极短时间的意思,而且儵忽是叠韵联绵词,不能分开二字解释。庄子寓言的意思,是浑沌不分浑沌存,凿开浑沌浑沌死。庄子是在寓言中强作儵忽之分,以南儵北忽对比中央浑沌,以大海兴波不宁对比中土安宁清净,其实是在暗示儵忽不可分。
这显示了道家与佛家在时间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区别。道家的时是整体的、无间的,虽然用倏忽表示时的短和快,但并不认为要作最小的计量单位去分割时间,而是更加强调时与事的合一。倏忽虽短,仍要包含事的发生,使时具有意义。佛家的时是构成性的、有间的,从一刹那到一昼夜,有计时单位,有结构形式,是以时论时,不管是否发生事情,时间可以得到分割。
无间,可以说是中国本源思想中对时的一个共同认识,而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则采取有间的态度。孔子与传说中的大禹时间相隔久远,但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他认为跟大禹之间没有缝隙、没有隔阂。庄子在庖丁解牛中讲“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虽是空间论述,以无厚度的刀入有缝隙的牛,作为一种哲学论说,也包括时的无间。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佛家的时间认识,与近代科学对物理时间的分解切割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中国本源思想与叔本华、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认识有一定的相通,强调时间的绵延性、内在性,以及时间与生命的同一性。这里不谈论无间、有间在认识上高下,只需记得物理时间对科学发展、心理时间(内在时间)对哲学认识各有特别价值就行了。
现在我们更多用瞬间来描述时间的短暂,而不太用刹那和儵忽。瞬间也不是一个计量单位,也是一个“无间”的时间片断,也是一个需要与事件合一的时间概念。我们不会平白无故地说到瞬间,没有事情发生,或者不是为了描述一件事情,我们就用不上瞬间这个概念。
单纯把时间分割成片断,那不是瞬间,而是消逝的时间空当。有事情在短时间发生来充实时间,才能形成一瞬间。因为拥有内容,瞬间才实在起来,生动起来,而不是像空白一样一去无踪,既无以形成真正的生命体验,也无以留下任何记忆。因此,一瞬间到底是多长,无可定义,它是一个不长的时间,但不可以用几分几秒来定义,而只能用事情的发生、高峰体验的完成等过程来定义。
生动的瞬间,具有持久化的潜力。我们可能在一个瞬间体验到生命的激情,或者感受到巨大的冲击,这些瞬间刻写了生命的历程,验证了生命的存在。瞬间虽然短暂,但它与现实生命直接结合,作为大脑的一份记忆被留存,从而具有持久性,直至他的生命停息,他的时间消失为止。可以说,瞬间是短促的,发生是一过的,在时段上它是流逝的,但它在生命体验中又具有回味和追忆的价值,在大脑中具有持存性。
作为一个时间单位,刹那如同分、秒一样,没有内容,它只丈量了时间,而倏忽和瞬间没有丈量时间,却具有生命的重量。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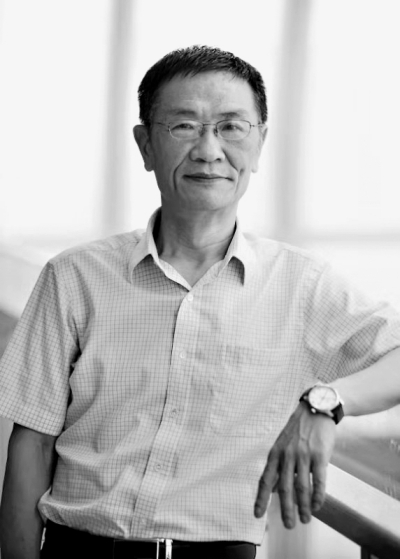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