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春枝
一
人类对高处的向往由来已久。吸万物之阳气、感天地之英华,自然崇拜、文化传统、强身健体、精神追求等多重因素,使登高与人类情感紧密相连。登高过程中,每一次挑战和突破都让人们深刻认识到自然的伟大和自身的渺小,领悟生命的真谛。具有浓郁家国情怀和强烈集体意识的中国文人,更赋予登高俯瞰别样和丰富的意义:或感慨历史兴衰更替,或念及个人际遇起伏,或浸染于眼前山河壮丽,情怀、块垒倾泻而出,化作笔下一行行隽永诗句。
建安十二年,曹操征伐归来,东临碣石,挥笔写下《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日月星辰、高山大海的浩瀚磅礴,映衬出曹操志在天下的抱负和胸襟。
公元696年,陈子昂随武攸宜征讨契丹,因谏言遭贬,登临燕昭王招贤的黄金台(幽州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感怀天地,忧愤交加。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心中郁闷,便有了“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抑郁之情隔着1200多年仍直抵人心。公元767年,已经56岁的杜甫因战乱四处流离、拖着病弱身体登上夔州长江岸边高台,“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倾吐其漂泊无定、晚景凄凉的境遇。
王之涣鹳雀楼上,观落日西沉、黄河入海,“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尽显豪迈与哲思。出自世家望族的崔颢黄鹤楼上,抬头看,晴空万里,悠悠白云;低头叹,高楼还在,黄鹤已去:“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游子的惆怅和思乡之情蓦然升起,成就千古名句。
公元1050年,王安石回江西临川故里,途经杭州飞来峰,登古塔,写下“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体现了正值壮年的他“变风俗,立法度”的气度和决心,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白一生游历四方,登临山水充满超脱凡尘的韵味。公元742年李白受权贵排斥,抱负难展,郁郁难舒,遂登至太白绝顶,“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这般超现实的瑰丽想象,不仅是与山对话、凌越自然,更是对心灵高远境界的飞升。杜甫登山之作则尽显沉雄气魄,早年科考落第后,他壮游泰山,一洗尘世烦扰,脱口而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气势磅礴,雄心毕现,不仅是对自然壮景的赞叹,更是早年雄心壮志的写照。
古人何以对于登高情有独钟?或许是因为深知生命的短暂和视野的局限,故而渴望在高处追寻更为广阔的天地与超脱的心境,在有限的人生里实现精神的升华和自我认可。高台、高塔和山巅,由此成了他们俯瞰尘世、眺望理想的绝佳之地。此外,中国自古便有登高可避灾祈福的古老俗信,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桓景登高避瘟的故事,被视为重阳节登高、佩戴茱萸等习俗的起源,这一传统绵延后世,融入民间生活,亦被诗人吟咏。王维那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便是此间情怀的生动写照。
二
即便在今天,人类对于天空的渴望、视野边界的拓展也从未止息。现代科技以其革命性的力量,赋予我们超越古人想象的“登高”之眼。2017年,中国首部全航拍系列纪录片《航拍中国》播放,利用先进航拍与8K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宏观视角,呈现了中国的地理奇观与人文全貌。屏幕前,亿万观众跟随着航拍镜头,在千米高空重新认识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其磅礴的解说与画面更成为经典教学素材。
这一空中视角的震撼,迅速催生了同类创作。2018年,新华社CNC推出《瞰中国》系列微视频,以每集60秒的精华体量,覆盖东北冰原、南方水乡、西北荒漠等特色地域景观,呈现长城、故宫等文化遗产的独特空中影像。节目在移动端和社交媒体播出后,获得了极大反响,迄今在新华社官网上还能看到《瞰中国》主题的更新视频。
可以说,这些航拍镜头代替人类挣脱地心引力束缚,通过直升机、无人机与卫星遥感的三维视角,将广袤的960多万平方公里山河浓缩成分秒之间的时空胶囊,在同一维度的航拍镜头下记录塞罕坝从漫天黄沙到浩瀚林海的蝶变,追踪长江江豚洞庭湖种群恢复的轨迹——这样的时空交替、动态展示是古人靠脚步丈量和登高无法企及的。即使仅论高度,现代无人机和直升机可达数千米,卫星遥感成像更将蓝色星球上的景观尽收眼底,远超李白、杜甫曾登临的山峰。超高清技术的加持能够捕捉到更多细节和美好,我们仿佛拥有了一双更为清澈深邃的眼睛,真正从云霄中领略“江山如画”。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实也有比无人机更高的视角去感受生活的这片土地。每次乘坐民航班机,我都会特意选择舷窗旁的位置,随着飞机不断攀升,大地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巨型画轴:山峦连绵起伏,像是大地隆起的一道道脊梁;峡谷神秘幽静,像是大地隐藏的一节节密码。广袤田野,是大自然用最细腻的针法勾织出的绿色绒毯;即使再宽阔激越的河流,也只是飘然于山川、田野之间青色或深黄的丝带。人类文明的痕迹——桥梁、道路、村落,在万米高空中,都微缩为细弱的笔画,点缀于自然之间。散落在山谷、湖泊、河流边的村落、民房,变成了一个个积木搭成的玩具,体现了人类逐水而居的特性。
若恰逢天晴,可以看到航线下的雪峰在阳光照耀下闪耀着圣洁的光芒,那些在地面上望而生畏的崇山峻岭,总会有几朵浮云缭绕于山顶,为嶙峋群山增添了几分柔美和神秘。若飞行于低空云层之上,则可见云海如棉花糖般蓬松、慵懒,偶尔露出云隙,大地若隐若现:黄土高原千沟万壑像被巨斧劈开的褶皱,裸露的黄土与稀疏的植被形成苍凉而壮观的景象;秦岭山脉轮廓巍峨,如果恰逢9—10月,层林尽染,针叶林与阔叶林交织成红、黄、绿的斑斓色块;关中、华北平原小麦、玉米田黄绿相间,阡陌纵横组成规整的棋盘格,人类的农耕文明竟能绘成这样巨大的几何图案。飞行在太行山上空时,山脉的轮廓会突然刺破云海显现,裸露的红色岩壁与苍翠的植被形成色彩张力。机翼下方锯齿状峰群,峰峰如刀砍斧削,山脊在阳光下投下锐利的阴影,与云层形成明暗对比。有的时候,机翼与峰顶的垂直距离可能仅数百米,感觉太行悬崖断壁几乎与机身平行,可清晰看到崖柏扭曲的枝干如铁爪般抓附岩壁。如果再凝视细瞧,会发现许多山顶或崖壁旁,间或有梯田和村落零星点缀,以细若游丝的道路在山梁间盘绕相连,人类繁衍、生存的韧性令人惊叹!
三
当飞机掠过我的家乡湖北上空时,千湖之省如一部古老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交织的华美乐章:长江九曲回肠,汉江清秀婀娜,交汇时泾渭分明,形成灵动的水网奇观:桥梁如弦跨江而过,滩涂与湖泊星罗棋布。仙岛湖、梁子湖、斧头湖、涨渡湖、东湖等如散落的宝石,环湖生态林延伸出翡翠般的韵律。稻田与鱼塘像被打碎的镜子,每块都倒映不同的天光和云朵,古云梦泽浪漫、神秘的气息草蛇灰线般流淌在荆楚大地的肌理里。夜晚的航班最美,从飞机上看城市群落,华灯璀璨时,如星河坠地,街市霓虹与桥梁灯光交相辉映,落入江河湖泊时,又交织出梦幻般的绚烂。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光芒,高速公路如珍珠项链将它们串联成网:北京的夜空被霓虹染成紫红色,中轴线上的建筑群在灯光中勾勒出首都的骨骼和气度。重庆高楼与山体错落交织,立交桥的复杂结构如发光的蛛网,在深邃的夜空映衬下加剧了“8D魔幻城市”的魔幻。当武汉三镇的轮廓逐渐清晰时,几座跨江大桥如银链、如彩虹横跨江面,东湖的沉沉碧水与两江四岸的彻霄灯火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山峦、河流、绿道、水榭、商圈、里坊、园区……每一处既有不同的节奏和调性,又相互呼应,形成一部城市空间与文化脉络完美融合的和声,彰显着中部龙头城市的繁华与活力。
高空视野给了我们直观、奇妙的体验,仿佛穿行于一粒时间胶囊里:前一秒还是高楼林立、立交盘旋、车流如织的现代都市,后一秒便闪回古城、古塔、古寺,黄泥红毡、青砖灰瓦的古建筑群。从黄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高峡到平湖,从荒漠到绿洲,从冰雪到海洋……大地也如同色彩斑斓的调色盘,一会嫣红、一会土褐、一会银白、一会金黄、一会青绿,跨越时空的景观切换往往在分秒内完成,每一段航程,都像在翻阅一本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地理画册。
当我从高空中长久地观看那些山脉的石纹和岩层在天光中显露沉积纪年的秘密时,一方面感叹造化钟神秀、个体如沧海一粟;一方面看到,盘山公路像解不开的绳结缠绕着山腰,某些我们引以为傲的改变,却像我们在地球上划开的一道道伤口,需要漫长的岁月才能平衡和修复。唯有从高空俯瞰才发现,覆盖山体的森林、高山峡谷间自然奔涌的河流、平原坡地上黄绿相间的植被和无人照拂的花朵,是大地最协调的颜色,也真正理解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事实上,即便我们身处万米高空,所见也不过是地球表面积的千分之三,这意味着我们错过了超过99.6%的地球表面。据说,唯有越过100公里的卡门线进入太空,看到的比例才勉强超过3%。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一次性能看到的比例约为11.6%,这已经是非常壮观的视野了,但仍然只是地球的一小部分。而在月球上,我们的地球不过是一个蓝色水球。旅行者1号回望时,它又变成了一个暗淡蓝点。所以,人类只有飞升到足够高的太空,才能真正从宏观上感受到地球作为一个完整星球的壮丽与渺小。正如中国空间站官网上那些由航天员拍摄的地球影像,每一帧,都凝结着人类探索宇宙的执着与艰辛。
地球与宇宙的广袤,远超我们日常所能感知的边界。即便乘飞机远行,所见也不过是星球的一隅。而在太空中,宇航员每90分钟可绕地球一圈,宇航员在“一日”内可见证16次日出日落——可见我们用以度量生命的时间,在更高的维度上竟如此不同。与之相比,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和焦虑在宇宙的时光隧道里微不足道。在地球漫长的生命史中,人类不过是匆匆过客。那么,在这白驹过隙的百年里,我们究竟该为这个诗意栖居的星球留下怎样微小而珍贵的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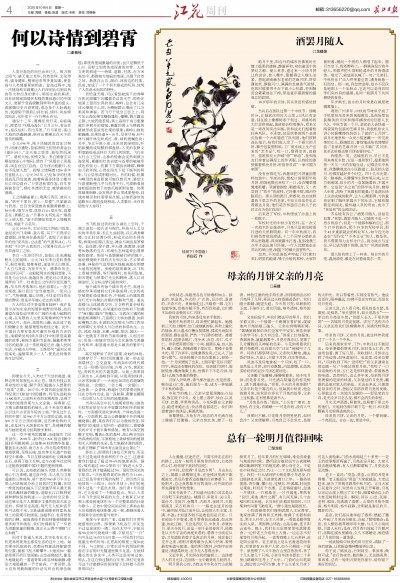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