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坦坦
我把吃——吃热干面,摆在我喜欢武汉的诸多理由之首,似乎正应了那句古语——“民以食为天”。
的确,“吃”在咱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首席之位,所以被称为“天”。这更体现在百姓的日常言行中,比如大家见面打招呼最常用的问候语就是“吃了吗”,尽管见面的时间与场合常常与吃毫不沾边,有时甚至是在公共厕所里,或者是刚刚从厕所里出来,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仍然这么问候。
“吃了吗”这句话有时候确实是问你吃饭了没有,但更多的时候和场合其实只是用来打个招呼,没有“吃”的涵义在里面,这一点是很让外地人甚至是外国人困惑与不可理解的。“吃了吗”用武汉话来说就是“吃了冇(mào)”,前两个字相同,后一个“吗”字变成了个“冇”字,两字声母相同,但语义则完全不同。“冇”算是武汉话中特有的一个字了,是“没”或“没有”的意思,因此“吃了冇”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吃了没”或“吃了没有”的问话。这是第一个区别——语义上的区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就是语音上的区别。武汉话中“吃”不念阴平声的“chī”,而念汉语拼音中的第三声上声“qǐ”。许多初听武汉话的人应该听不懂“qǐ”(吃)这个字,就好比我初到湖北襄阳时听到当地人把鞋子(xiézi)念成“hái zi”——武汉人也是这么说的,心想鞋子怎么成了“孩子”呢?这就是方言的有趣之处。武汉话中还有许多有趣的东西可以讲,武汉话其实也是我喜欢武汉的理由之一,但因为这一篇的主题是热干面,所以就不展开讲了。
还是言归正传,“言”热干面。
吃了这么多年的热干面,可真要我说说它的来龙去脉,还真说不来,只知道个大概。好在现在上网方便,随便一搜就搜得出来。
说是热干面源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汉口长堤街卖汤面的黄陂蔡榨人蔡明纬。他的汤面做得非常受欢迎,客人经常排队要等很长时间,很多客人等不及走掉了。由此,蔡明纬摸索出一套“掸面”的工艺——先把面煮七八成熟,然后快速降温并均匀抹上油,这样卖面时出货量就快了。后又将芝麻酱加进面里,身边的人都说好吃。热干面——这个武汉人民最爱的小吃就这样诞生了。
热干面现在是武汉最出名的小吃,网上说它是“武汉最出名的小吃之一”,但我把“之一”给删掉了,因为它就是“最”,不是“之一”。如今的热干面与兰州拉面、山西刀削面、四川担担面、河南烩面并称“中国五大名面”。有一年我去伦敦,在唐人街上看到“中国五大名面”的招牌,其中赫然就有热干面。可见热干面不仅“吃”在中国,也“吃”到了世界。
那热干面为什么就能力压群“吃”那么“火”呢?
我不做餐饮,也不懂餐饮,因此无法从烹饪技艺的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是从一个食客的角度来解释一下热干面“火”,确切地说是它普及并为大众喜闻乐“吃”的原因。
首先是吃起来简单。所谓“吃起来简单”,又包含两个方面的“简单”:一是食材简单——就是面,加上卤水汁、芝麻酱、食油、辣椒油、葱、蒜、萝卜丁、酸豆角、酱油、醋等辅料佐料。其中卤水汁、芝麻酱、食油、酱油甚至醋都是给你添好了的,不需你手劳,你需要取舍的就是葱、蒜、萝卜丁、酸豆角这几样,这几样完全根据各人口味予取予舍。再就是“端”得简单。所谓“端”得简单,就是热干面是“干”的面,几乎没有汤水,因此你端起来就可以走,不用担心像汤面那样会有汤水泼出来,而且可以一边走一边吃。以前武汉早上的一大风景就是许多人一边匆匆赶路上班,一边手里还端着碗热干面大吃特吃,走路吃饭两不误。当然现在建设“文明城市”,这种“风景”已经很少能看到了,就像现在有了空调,就再也难见竹床阵一样。
其次是做起来简单。我是个舞文弄墨的,但只要我愿意,我明天说不定就可以搭个棚子、支个炉子卖起热干面。因为制作热干面的设施确实是忒简单了,唯一考验人的,估计就是身体和作息了——需要身体好也需要早起。仅此而已吧!当然味道是不是正宗是不是好,那就另当别论了,要做好肯定要积累经验。
第三是便宜。记得20世纪70、80年代,热干面一碗只卖一两毛钱,90年代涨到大概大几角、块把钱一碗吧,现在大概四五块钱一碗。前几年汉口万松园一带的雪松路美食街热干面创新,推出“蟹脚热干面”,76块钱一大碗,相当于一盘大菜,可以供几个人吃。但总的来讲热干面依然是价廉物美的大众食品,较拉面、刀削面、担担面、烩面甚至襄阳牛肉面等其他面食,仍然是最便宜的。一个便宜三个爱,何况味道还这么好,焉有不大卖之理!
我第一次吃热干面,记得是1974年的冬天。那一年我们全家回安徽老家,顺便沿长江旅游:从襄阳到武汉,再坐“东方红”号客轮到南京、上海。我就是在途经武汉时第一次吃的热干面。
当时我父母都是现役军人,按照当时部队的规定,我们一家可以免费住部队的招待所。当时中山大道与民生路交会的地方有个部队招待所,离那不远的地方,也就是老亨达利钟表商店的对面,就有一家“蔡林记”热干面馆。几步之遥,我就是在这里吃了我人生的第一餐热干面。这一碗热干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面,确切地说,是这样干的面。我出生在山西大同,山西人喜欢吃面,我自然也不例外,但山西的面,包括后来在襄阳吃的面,都是有汤有水的,可这碗面却一点水也没有,干涩干涩的,还有点麻口,但因为加了芝麻酱、香麻油等而回香无穷。以至于离开武汉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回味它那种干涩麻口但回香无穷的味道。不过从那以后,再没吃上热干面,直到1981年我来武汉读书工作。
热干面虽然是传统小吃,但也并非一成不变,总有商家因为想卖出新意而常常思变。近年来热干面最著名的一大“变”,就是前面提到的“蟹脚热干面”,它一经推出即成爆款。每有外地朋友来汉想吃热干面,我总是推荐他们去那儿,也带人去吃过几次。然而“蟹脚热干面”虽然好吃,但终究不是普通消费,只是作为热干面中的“极品”,偶尔尝尝可以。
关于热干面,我就先讲这么多吧。有些与热干面有关,有些看似与热干面无关,但其实与热干面还是有关。因为热干面已经不仅是一款美食,更是一种文化——汉派文化,它尤其是武汉这座现代宜居城市里市民生活的直接产物,有着深深的市民印记。吃热干面,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
外地的游人来到武汉,无论是在繁华的闹市,还是在偏僻的里巷,都请记得找一家小店。记得哦,一定是一家小店!然后坐下来,来一碗热干面,最好再配上一碗蛋酒,然后,一筷一筷慢慢地嗦,一口一口慢慢地咽,这一嗦一咽之中,你就尝到了地地道道的“武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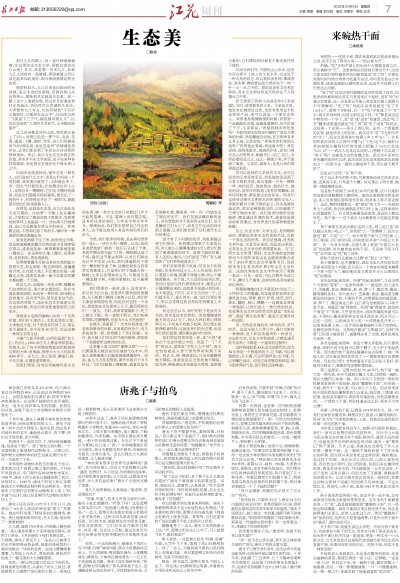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