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记者 马梦娅
美育之重,重在其“无用之大用”。它关乎一个人如何理解生命的意义、一个民族如何守护精神家园、一个时代如何定义文明的高度。
近日,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高校美育教指委副主任委员杜卫出版新著《谈美育》。长江日报《读+》专访杜卫教授,他指出,美育的本质是“育人”,而非培养艺术家。我国拥有极为丰富的美育思想,在当下,美育回应时代需求,又具有了新的意义。
美育是创造教育,激发生命活力,培养人们的独创性和创造性直觉。在智能时代,美育塑造了人的独特精神特质,培育出AI无法替代的核心素养——对美的情感共鸣、个性化的审美体验与超越性的创造能力。
■ 美育要有
“妈妈的味道”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杜卫从事高校教育四十余年,常与师生们分享一个有趣的观点:“教育的方向,既要‘做爸爸’,更要‘做妈妈’。”“做爸爸”,是指教育要给孩子立规矩、传知识,帮他们掌握安身立命的本领;而“做妈妈”,核心是把孩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这份健康不只是健康的体魄,更有丰盈安稳的心灵。
杜卫在新著《谈美育》中,用“妈妈的味道”来解释美育的育人机制:“一个人从小就会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被塑造特定的味觉喜好,从家里至亲做的饭菜再扩展到家乡的饭菜会使人形成特定的味觉喜好,我们可以把这种喜好说成对‘妈妈的味道’的眷恋。我们成人后走向四面八方,妈妈的味道却一直是我们对家和家乡眷恋的一部分……这味道里包含了对家和家乡的深情。此刻的味道既是感性经验,又具有人文内涵,而且这种人文内涵是沉淀在感觉经验之中的,几乎成了一个人的文化本能。美育的深刻育人机制在于,通过审美经验的积累和审美素养的养成,塑造了人们审美的知觉、想象、体验方式。”
他在书里写道:我们要想让儿孙们拥有一颗中国心,最理想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从小背诵优秀的唐诗宋词,让他们去祖国各地的博物馆观赏精美的文物,或学书法,或听戏曲,或读国画,游历祖国山山水水,品尝各地特色美食……这样,他们的感官都被中国文化反复浸润过了,祖国优秀的文化基因也就内化到了他们的心底。
如今的教育里,“爸爸”的角色做得不算少。大家默认教育就是“教知识”,而且得是客观、可重复、能标准化的知识——一首优秀诗歌的赏析被框在固定套路里,孩子想法不同就被判定“不正确”,这样的场景并不少见。
教育应该有“妈妈式”的体恤。杜卫指出,教育不可太单一,只重智育而忽略五育并举,培养出的人才会趋于扁平,没有全面立体的成长。
美育最懂“妈妈式”的关怀——它不纠结功利,只关心孩子当下的精神状态。孩子欣赏一幅丰子恺的画,能从简洁笔墨里感受到慈爱与亲切;读一首《诗经》,能在“关关雎鸠”里体会最本真的情感。这些体验带不来直接的分数,却能让孩子在审美中获得快乐,滋养出健康的心理。这种对“当下幸福”的关注,正是“妈妈式”教育的核心,让教育更完整。既重理智培养,也重感性滋养;它能通过优秀艺术品里的鲜明个性和创造精神,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访谈】
■ “趣味无争辩”,品位有高低
读+:请您简单介绍我国美育的发展脉络,其间有哪些关键节点,又有哪些代表性人物与故事能体现这一脉络?另外,与西方美育思想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育独特之处是什么?
杜卫:中国美育发展的脉络,其实是一条“传统积淀与西学东渐交织”的路径,既有千年文化的根基,也有近代以来的革新。
中国的美育思想源头非常早,虽然“美育”这个明确的概念是20世纪初才引入的,但早在先秦时期,“诗教”“乐教”就已经承载了美育的核心功能,这是我们传统美育的根基。当时的儒家思想里,美育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和道德教化、人格养育紧密绑在一起的。
比如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实就是把诗、礼、乐作为美育的重要载体,最终目的是培养“文质彬彬”的理想人格。那时候没有“美育”这个词,但这种通过艺术和情感体验来塑造道德人格的实践就是最本土的美育传统,它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渗透在文化教育的方方面面。
到了20世纪初,这是中国美育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西方美育理论被引入,让美育从传统的“诗乐教化”升级成一门独立的学问。这里有两个绕不开的人物,王国维和蔡元培先生。
王国维撰写了大量关于文学、艺术和美学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孔子教育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从情感和艺术的熏陶开始,最终在“乐教”中完成理想人格的塑造。王国维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理论,而是用西方的美学框架重新阐释中国传统的“诗教乐教”,把本土思想和外来理论打通了,让“美育”这个概念能在中国文化土壤里扎根。
蔡元培先生把美育提升到了国家教育方针的高度,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当时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他希望通过美育来培养国民的健全人格,摆脱封建宗教的束缚。他的核心思路也是融合中西,一方面吸收西方美育对“健全人性”的追求,另一方面延续了中国传统美育的道德内核,让美育成为改造社会、培育国民的重要手段。
西方美育理论的完整提出,来自18世纪末的席勒,他写的《美育书简》是西方美育的经典著作。席勒提出美育的针对性很明确:当时工业革命兴起,科技发展让人们的理性思维越来越发达,但感性、想象力、情感这些方面被压抑了,导致“人性分裂”;同时商品经济盛行,利己主义抬头。所以席勒的美育有两个核心目标:一是调和理性与感性,解决人性分裂的问题;二是通过审美培养人的共情能力,克服利己主义,让人成为“审美的人”,进而成为“道德的人”。
而中国传统美育,包括20世纪初我们引进西方理论时的侧重,都和西方有明显不同。最核心的独特之处,就是从始至终以“道德人格的塑造”为核心目标。我们的“诗教”“乐教”,从来不是为了单独培养“感性能力”,而是通过诗词的意境、音乐的韵律,让人们在情感体验中理解“礼”和“仁”的道理,比如《诗经》里的“温柔敦厚”,就是通过诗歌熏陶培养人的仁爱之心和君子品德。
读+:我们经常用“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趣味无争辩”“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等来描述艺术评价的主观差异性。审美趣味是个性化的,我们应该如何在这样的差异中推进美育?
杜卫:“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趣味无争辩”,这确实道出了审美趣味的个性化特征。每个人的天性、生活与学习经历不同,形成的审美偏爱自然有差异,从这个角度讲,尊重个性差异是美育的前提,毕竟多样的趣味才能让审美世界更鲜活,也为创造力发展打下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审美趣味无需培养,相反,正因为有差异,我们更要在尊重个性的同时,找到提升审美趣味的路径。
首先得明确,审美趣味的差异是相对的,它有“共性边界”和评价标尺。不能说只要是个人偏好就都合理,比如过去对“三寸金莲”的病态追捧,或是现在一些“娱乐至死”的庸俗趣味,这些脱离了审美价值本质,甚至违背健康价值观的倾向,显然是需要引导矫正的。即便是在审美价值范围内,趣味也有高低广狭之分:只喜欢肤浅的娱乐性内容,对经典作品毫无兴趣,或是只盯着某一种艺术题材、某一位艺术家,排斥其他审美类型,这些都是趣味不够高、不够广的表现。好的审美趣味,应该能感知艺术作品从感觉、形式到情感意味的多层价值,这是我们培养美育的重要方向。
具体到培养方法,核心还是要依托优秀经典作品。经典作品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审美标杆”,具有典范意义。像《诗经》流传几千年,历代的注解、阐释让它的审美和人文价值不断积淀;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经过无数指挥家、乐团的演绎,还有各类学术研究的深挖,内涵早超出了原初乐谱。教育者要帮学生们建立审美价值的“基准线”,知道什么是真正有厚度、有深度的美。
美育不是要把所有人的趣味变得一模一样,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帮每个人把审美趣味提得更高、变得更丰富。
读+:在您看来,美育区别于德育、智育、体育的独特价值是什么?
杜卫:美育的根本作用对象是人的“感性素养”,这是其他几育替代不了的。
智育主要发展人的逻辑思维和认知能力,追求的是“真”,比如学数学、物理,练的是理性分析和判断;德育靠的是道德规范的引导和意志力的坚守,追求的是“善”,是让人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守住道德底线;体育侧重身体锻炼与体魄塑造,同时也包含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培养,比如长跑需克服极限痛苦、团体项目强调团队合作,其核心是身体与精神的协同发展。
美育不一样,它专门培养人的情感能力、想象力和审美感知力,追求的是“美”。这种美不是靠逻辑推理推出来的,也不是靠意志力硬撑出来的,而是靠情感去体验的。就像练书法,虽然也有肌肉记忆,但最终是要通过笔墨的韵味引导人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重点在心理和精神的滋养。这里得强调一句,“侧重”不是“偏废”,美育也会触及身体层面,比如绘画时的手部动作,但核心始终是感性素养的培育,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三育最根本的特质。
除了作用于感性,美育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特点——超功利性,也就是审美时不考虑个人利害。举个例子,一片树林,植物学家看的是树龄、生长状况这些科学认知;木材商人算的是市场价格、盈利多少,全是功利考量;但画家或诗人看的,是树林的色彩、排列的美感,会联想到白桦林像保卫祖国的哨兵,这种想象和感知不产生实际的“用处”,不能换取金钱价值,却能让人获得心灵的自由和愉悦。这种超功利的体验,是其他三育很难提供的,也是美育独有的精神价值。
■ 美育的“无用之大用”,核心在于培养“完整的人”
读+:在您看来,当下为何要强调“以美育人”的重要性?
杜卫:强调“以美育人”,首先就在于美育是德育的“沃土”,能解决当下道德教育中的一些关键问题。道德成长不是从抽象的理念灌输开始的,而是从情义和真诚的情感发端的。许多哲学家和教育家都认为,德育要建立在美育的基础上,先通过美育陶冶情感、让心灵和谐,才能在这片沃土上培育出真正的道德。
美育的超功利性还能帮我们纠正利己主义的倾向。道德的本质是利他的,而审美时那种不考虑个人利害的体验,能让人跳出功利的算计,学会共情和包容。
当下社会节奏快,功利化的倾向容易让人变得浮躁,只看重实际利益。这时候强调“以美育人”,就是通过感性的滋养、精神的愉悦,让人们在审美中获得心灵的安顿,培养出有真诚情感、有利他之心的健全人格——这正是当下我们最需要的,也是美育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读+:美育这种“无用之大用”究竟“有用”在哪?
杜卫:美育“无用”——美育不能直接让你多考几分、多赚多少钱,不能立刻转化成看得见的利益,这是它的“无用”。但这种“无用”里藏着最根本的“大用”,核心就在于它塑造的是人的精神底色,是其他教育替代不了的。
第一,这种“大用”体现在对抗功利化带来的精神贫瘠。现在很多人凡事都问“有什么用”,把自己困在功利的圈子里,活得浮躁又疲惫。美育恰恰提供了一个“无用”的出口:欣赏一幅画、听一首曲、看一片晚霞,这些都不能换钱,但能让你暂时脱离算计,获得心灵的自由和愉悦。这种精神滋养,能让人在功利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的安宁,不至于变成只追名逐利的“工具人”。
第二,它的“大用”还体现在培育人们的创造力与个性。功利化的教育容易培养标准化的人才,而美育是个性化的——每个人对美的感受和理解都不同,这种独特的感性体验是创造力的源泉。AI能生成标准化的作品,但它不会有丰子恺画里那种独有的慈爱,不会有诗人面对白桦林时的独特联想。这种源于“丰厚感性”的创造力,是推动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这难道不是最大的“用”?
第三,它的“大用”更体现在塑造健全的人格。就像之前说的,美育是德育的沃土,能培养真诚的情感;而在AI时代,它又能帮我们守住人的“感能”优势,让人保持作为“人”的温度和尊严。这种既能对抗功利浮躁,又能培育创造力和健全人格的价值,看似“无用”,却决定了一个人能走多远、活得有多丰盈,也决定了我们在科技时代不会迷失自我——这就是美育“无用之大用”的真正内涵。
我始终强调美育要培育“丰厚感性”。“丰厚感性”不是单纯的情感泛滥,也不是感性压倒理性,而是一种融合了审美知识、审美能力和审美态度的复合型感性素养,里面其实暗含着理性的沉淀,是“感性中有理性,理性滋养感性”的状态。如在欣赏一幅古典绘画时,既需凭借感性捕捉画面的色彩与意境(感性层面),也需运用审美知识分析构图技巧与时代背景(理性沉淀),这种感性与理性的交融便是“丰厚感性”的体现。
审美态度是“丰厚感性”的灵魂,是追求生活的艺术化。比如看一片落叶,不只会想“这叶子没用了”,还能感受到它的纹理之美,联想到生命的轮回,这种不被功利束缚的心态,本质上是理性对感性的解放——让人跳出“有用没用”的算计,用更丰富的视角看待世界。
在AI时代,这一点更关键:科技已经能替代大量简单重复的理性劳动,可机器没有真正的情感体验,没有审美时的感动和创造。美育的“无用之大用”,在于培养人们的“感能”,使人成为“完整的人”,在将来,这很可能就是人的核心身份标志。
■ 坚守人文立场,将AI打造成美育新工具
读+:随着科技发展,AI可以迅速在技巧层面完成艺术创作。人类学习艺术的意义会被其影响削弱吗?
杜卫:美育本身就是人文教育,是基于审美经验的人文教育。科技越是发达,人类越是需要人文精神。这一方面可以制约科技的野蛮生长,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保持适度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多方面的,例如贫富差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感性与理性、传统与未来等。这是美育的一种与高科技之间的反关联。
反关联不是反对科技,反科技不仅是徒劳的,也是非理性的。反关联讲的是与高科技处于一种辩证关系,一种制约、补充和联系的关系。高科技的底层逻辑是资本逻辑,美育是一种人性的力量,它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幸福和人性理想,这一点恰好可以弥补高科技的不足。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且协调平衡的社会形态,人文精神是不可或缺的。
人工智能会导致艺术消亡吗?可能会使大量缺乏创造力的人工艺术品消亡,因为人工智能可以大量制作和复制这类作品。但是,艺术活动是人工智能不可替代的。艺术活动存在于欣赏者或者创造者与世界的互动之中,我们看一幅画而产生审美经验,这完全是个体的、主观化的、即时性行为,人工智能不能替代人去鉴赏和创作。
人工智能与美育也可以有正关联,那就是把它当作工具,提升美育的效能。例如,人工智能强大的生成能力有可能使世界经典艺术的数据库建设成本大大降低,极大地提高美育资源的全球可及性。这对于欠发达地区美育的开展可能是有助力的。还有,在数字化平台上,个体可以做各种具身化的艺术创造,增加人们获得审美经验的途径,简化获得审美经验的方法。
回顾人类教育史,教育的内涵包含变与不变的维度。变的是适应不同时代现实对人才的特定需求,不变的是培养符合人类共同人性理想、追求“全面发展”的人本主义核心目标。前者是教育的工具性,是技,后者是教育的目的性,是道。如同人类的历史,真善美、爱与和平是亘古不变的价值追求。
读+:我们应如何将AI打造成美育的“新工具”,并与之建立健康、创造性的关系?
杜卫:AI作为美育的新工具,它在素材整合、形式呈现等层面提供不少便捷,但有个核心前提必须明确:AI的工具属性始终要服务于美育培育“丰厚感性”的根本目标,绝不能替代人的审美经验。
从美育的本质来讲,它是基于审美经验的人文教育,AI作为技术工具,既生成不了真实的审美体验,也替代不了人对艺术的情感共鸣与精神感悟——但它高效的功能,确实能成为美育的有益补充,比如帮着呈现不同风格艺术作品的对比、还原经典创作的时代背景,为大家积累审美经验搭个便捷的梯子。
引导人们和AI建立健康、创造性的关系,关键还是要坚守人文立场,不能让技术消解了审美的本质。AI是“辅助手段”,不是“核心主体”,人的审美经验积累永远要放在第一位。我们借着AI发展,要强化大家的审美批判性和主体性。美育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培育审美自由和批判性思维。技术复制和人文创造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对比中把“人的审美”和“机器的生成”的边界搞清楚,就不会陷入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反过来,也可以用AI工具激发人们的创造活力,比如让AI帮着整合多元素材,再引导大家注入自己的情感、审美态度去二次创作。
说到底,美育的终极指向是人的精神成长和人性完善,AI时代更要把“人该成为什么”这个问题想明白。AI的价值是解放那些重复性劳动,而人的独特优势,从来都是深刻的情感体验、共情能力和超越性的创造。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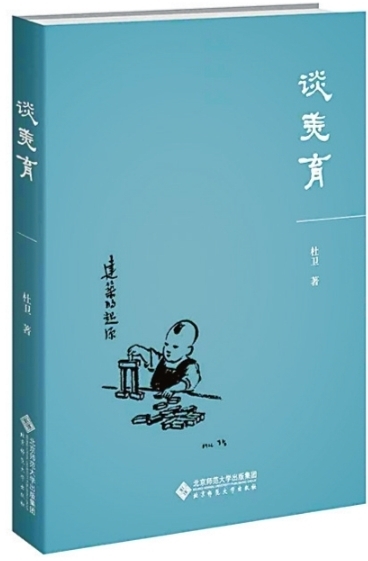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