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观中国:1930年代的中国人、中国事和中国景》是一部关于中国游记散文类的著作。作者路易斯·拉卢瓦置身几千年历史的文明之国,强烈感受到中国传统音乐、哲学、风土人情、习俗礼仪带来的美好体验。作者借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亲身交往和接触(上至孙中山、梅兰芳等政治和文化名人,下至平民百姓),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中国事和中国景,为中西文明互鉴提供了历史见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也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拉卢瓦于1874年生于法国上索恩省格雷市,1944年卒于汝拉省多勒市。拉卢瓦1893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于1896年获得文学学士文凭,1904年以题为《亚里士多塞诺斯与古代音乐》的论文获得博士文凭,成为第一位取得巴黎索邦大学音乐博士学位的人。他曾在巴黎索邦大学及巴黎音乐学院教授音乐史等课程,并撰写大量音乐评论。1913至1940年担任巴黎歌剧院院长。他曾撰写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若干,涉及戏剧、音乐等不同主题。
关于中国书法,拉卢瓦在书中《北平第一日》这一章节中谈道:“书法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这些白色布幅上书写的大字,没有任何其他衬托,只有笔画和字所包含的意思,就已堪称杰作……世间万物就是一个个象形文字,艺术家通过具有特殊意义的行为使之重现,我们应该像读诗那样去欣赏一幅画作。静止的空间只有在隽永的凝固中流动起来才会迸发出生命的神采。”他指出:风骨,是书法应当具备的神韵。“不管分散聚拢还是此撇彼捺,总保持一定的顺序,这是肋骨和胫骨,那是脊椎和髌骨,油亮的浓黑色定下了轮廓,停顿片刻再次起笔,留下一片墨迹如云如雾。”
除了中国书法之外,中国的音乐、绘画、饮食等传统文化,拉卢瓦在书中都有论及。他置身几千年历史的文明之国,强烈感受到中国传统带来的美好。
在西方不同时代、数量可观的中国游记中创造的“中国形象”,无疑是中西交流史上一面巨大的镜子,从中显示出的不仅是“中国形象”创造者自身的理想和文化积淀,也是西方视野下色泽斑斓、内涵丰富的“中国面影”。
■ 天坛【节选】
中国思想中天生具有对称的观念,始终尊崇建筑的实在感和周围环境的虚空感。除了破屋成片的城郊(就像欧洲),在其他的地方,包括乡村,都保留了这种虚实的空间对比。房舍围绕公共水井而建,院子和菜园之间留有适当的空间。中国的房舍需要呼吸的空间。
孔教中的神与古代异教神话中的神不同,并没有人形,因此不需要凡间的居所。早在孔子之前,人们就用咒语召唤江神河伯、雷公电母,还有掌管水和空气的神龙,这些神可以幻化成各种匪夷所思的形态。儒教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些信仰,但将其完全排除在皇家祭祀之外,而只保留了先皇牌位和几个最高等的神灵。比如标志四或五个方位基点的山峰,这些山峰本身就是大自然造端的神殿,天圆地方则分别象征半球穹顶和地面的四个方向。天地相对恰好与阴阳对应。冬至阳气回升,太阳偏天之南,在城南祭天;而夏至阴气始至,背阴为北,在城北祭地。
在君主制结束之前,皇家祭祀的队伍在冬至寒冷的早晨从这里缓缓走过,前面一座代表苍天的圆形祭殿以大理石为基座,屋顶微微内陷,皇帝在仪式的前一夜来到这里,无比虔诚而谦卑,静静地默思。稍远处的叶丛下是一排琉璃瓦的商铺,专门售卖丝制钱币,供人投入支在地上的火盆中焚烧,这些粗糙的铜锅大小足可容下一人。
圜丘台立在三层巨大的圆台之上,底层直径约为上层直径的两倍,各层四面的台阶面对四方,坐落在环形围墙之内。
《易经》以和弦和音管大小的比率为基础,建立了一种数字理论的规则,就像毕达哥拉斯(古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理论,只是两种理论的运算法则不同。《易经》中偶数对应阴,单数对应阳,其中九为至尊之数。所以在这个冬日的清晨,我像当年的皇帝一样站在圜丘中心,看到周围的石台犹如平放的巨大车轮。以扇面铺开的石板分成九块,每个扇区由九排石板组成,第一排一块石板,第二排两块,第三排三块,如此递增,直至含有九块石板的最边缘一排,共计四十五块,也即九五之和,五是《易经》数字理论中另一个重要数字。扇区最外围共有八十一块石板,是九九相乘之和。正如西方的数学家所说的,将一个数字乘以平方即是对其价值的加倍肯定。
磨损的石板看起来不那么齐整了。扶手上一块新雕的大理石已经摇摇欲坠,被一根铁线固定住。祭殿已经废弃不用,但仍屹立在苍穹之下,九九和谐让它成为上天在人间的镜子,在人间的无声神曲。
祈年殿内饰有星辰图案的木雕圆顶如同苍穹,藻井正中刻有龙凤雕饰,振翅高飞的吉祥凤凰身旁环绕一条象征至高权力的金龙。十二根金柱平地托起大殿,象征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主持典礼的皇帝进入象征万世的殿中拜天,祈求超越空间乃至时间的神力。而根据一种仅仅由知觉所至的构想来看,这种神力或许真的存在。这种构想与现代物理经过无数次数学运算于近期得出的构想相类,后者在三维空间之外加上了第四维——时间。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整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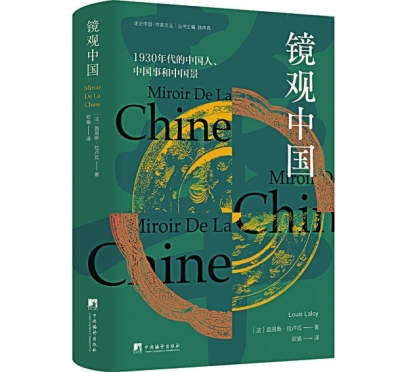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