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平原
几个月前,我给若干友人发去约稿函,扣除技术性的说明,最最关键的是以下这四段话:
从ChatGPT横空出世,到DeepSeek震惊全球,短短几年间,人工智能从一个高深的专业领域,变成一个狂欢的全民话题。从政府到民间到学界,各行各业,无论持何种政治/文化立场,此刻或日后,都将受其深刻影响。作为大学教授,尤其是人文学者,对此自然格外敏感。
世界史上,每次特别重大的科技进步,都会伴随一定的价值重组、社会动荡,以及知识结构的变迁。这回自然也不例外。若干年后,震荡期过去了,回头看,今天的好多想法与论述,很可能显得幼稚可笑。但那是真实存在的人类寻路的迷茫、痛苦与挣扎,值得尊重与保存。今天的所有思考与表达,都当作如是观。
在此意义上,才能理解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为何会得到如此广泛的社会反响。北京大学出版社甚至剑及履及,商请我主编书稿,聚焦“AI时代的文学教育”,及时回应这一影响深远的重大时代课题。
考虑到巨大的冲击仍在进行中,离达成社会基本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我们的杯子又如此的小,遂决定量力而行,仅仅聚焦大学里的“文学教育”。这个题目内含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深刻反省,以及对于文学教育的宗旨与目标、课程设置与教学方式、论文要求与学术伦理等的重新思考。
约稿得到热烈的响应,只是到了截稿时,好几位朋友临阵退却,说不是没兴趣,而是想得太多了,不愿仓促应战。其实,即便已经交稿的,连同我这个主持人,何曾不是落笔为文时战战兢兢?但就像约稿函说的,正是这些深一脚浅一脚、只有大致方向而无详细路线图的探索,体现了“真实存在的人类寻路的迷茫、痛苦与挣扎”。
我阅读本书书稿的第一印象竟然是,诸君为文时,为何那么喜欢使用问号?不管是正问还是反问、是犹豫还是疑惑,是转折还是感叹,最大的底色是“不确定”。这其实很正常——既然刚刚起步,多问几个“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没什么不妥。反而是斩钉截铁的感叹号,容易让人心生疑惑。
我说的“不确定”,不只是全书各文视野及立场存在较大差异,还包括同一作者行文中的犹豫与顿挫。面对昔日熟悉的话题,比如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以及文学教育,如今也都如雾里看花,说话的口气不再那么笃定了。这样也好,大家彼此彼此,谁也别笑话谁,那就尽可能切己,直陈你我当下真实的感受。若干年后,尘埃落定了,那时再来谈共识、下结论。
阅读三十三篇学友提交的文章,真的是获益良多。有人深沉,有人激昂,有人惊叹,有人彷徨,长文短章,都是有感而发,其中不乏玄谈与隽语。略为斟酌,决定将所有文章根据内容,分成以下四辑:第一辑“AI与人类命运”,第二辑“AI与诗文写作”,第三辑“AI与人文教育”,第四辑“AI与课堂教学”。其实,好些文章纵横驰骋,涉及多个话题,之所以强行归类,只为便于读者查阅。好在分类只是外在的标签,善读书的,从来不受此限。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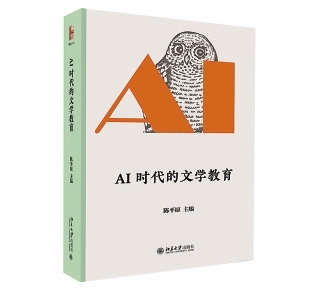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