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前进
我攥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站在晒谷场边,稻穗沉甸甸的香气混着汗水的咸涩,在记忆里酿成一坛五味杂陈的酒,那一年是我最后一次全流程参与“双抢”。“双抢”二字,听起来颇有些军事行动的意味,实则不过是农民与天时的角力罢了。“春争日,夏争时”,双抢是一场和老天爷的赛跑——七月中旬到八月初,金黄的稻子熟透了,必须赶在暴雨倾盆前收割完,不然半年的辛苦就全泡了汤;与此同时,秧田里的晚稻苗也急着下种,错过了农时,秋收就成了泡影。双抢也是一道几何题:梯形的草帽遮挡圆形烈日,平行四边形的水田里,父亲用等差数列的速度插秧。
七、八月的鄂东丘陵像一口沸腾的铁锅,蝉鸣在滚烫的空气里炸开。
双抢的锣声总是在晨光熹微时敲响。天还没亮透,父亲便带着我和妹妹扛着月牙般的镰刀出门了,露水把裤脚浸得透湿。母亲在灶台前煮一大锅糙米粥,柴火噼啪作响,火星子在黑暗里一闪一闪,像极了她眼角未干的泪。
“小暑割不得,大暑割不撤”。稻田里,金黄的稻穗低垂着头,仿佛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又似在默默承受着盛夏的热烈。那一片片稻田,宛如金色的海洋,在微风的轻抚下泛起层层波浪,仿佛是大自然馈赠给这片土地的壮丽画卷。而在这幅画卷背后,是那一年一度紧张而忙碌的“双抢”时光,抢种与抢收,构成了农耕岁月里最急促的节奏。
来不及欣赏这幅“稻田画”,我们就要赶在太阳在伸懒腰的时候割稻子。“稻田画”被我们擦去不到一半,太阳就像悬在头顶的火盆,烤得稻田里的水都泛着白晃晃的光。这时候,母亲带着煮好的糙米粥、粑皮子(用面粉做的类似煎饼类的干粮)和一些咸菜来到田边了。我蹲在田埂上错峰就餐,稻叶边缘的锯齿在手臂上刻下了细密的血痕,汗水一浸,火辣辣地疼。我看着父亲弓着背,镰刀在稻秆间划出沙沙的声响,汗水顺着他黝黑的脊梁滚下来,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远处,母亲已经割出了一小片空地,金黄的稻茬整齐地排列着,像被梳子梳过的头发。
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恰好在田里割稻子。有人向我母亲道喜,她直起腰来,抹了把汗,只说了一句:“稻子不等人啊。”便又弯下腰去。通知书被随手放在田埂边的衣服堆上,上面已经沾了几个泥点子。
“赶紧的,把水壶拿来。”父亲的声音从稻田里传来,沙哑得像被太阳晒裂的土地。我赶紧跑过去,递过那个印着“劳动光荣”的军用水壶。父亲接过去,仰头灌了一大口,水顺着下巴滴在衣领上,很快就被晒干了,留下一圈白色的盐渍。镰刀划过稻秆的沙沙声,是那个夏天最熟悉的旋律。我握着镰刀的手很快磨出了血泡,汗水流进伤口,火辣辣的疼。父亲却总说:“这点疼算什么?你要是吃不了这苦,以后怎么在大学里熬出头?”
“天地汗蒸房,铁肌咸泉涌”。中午时分,太阳毒辣得简直要把人烤熟。我们会尽量找一个树荫下吃饭,饭是早上吃剩下的糙米粥,已经凉了,菜也主要是素炒黄瓜、烧茄子、辣椒炒豇豆,还有又咸又酸的腌菜,我们就着凉粥将它们骗进肚里。远处传来知了的鸣叫,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人的耳朵刺穿。母亲擦了擦汗,叹了口气:“今年这天气,真是要命。”
偏偏这个季节的雨水又多得出奇。方才还是烈日当空,转眼间乌云密布,豆大的雨点便砸了下来。我们只得丢下手中的活计,仓皇奔向田埂边的草棚避雨。雨水打在稻穗上,沉甸甸的稻谷便垂下了头,若不及早收割,便要发芽霉烂了。雨过天晴,田里的水汽蒸腾上来,与尚未散尽的热气搅在一起,人在其中,如入蒸笼。常常是刚割完稻子,一场暴雨就把田里灌得满满当当,第二天又得放水晒田,重新开镰。雨停后,我们又匆匆赶到田里。水已经漫过了小腿,父亲赤脚站在水里,用手测量水深。“得赶紧放水,不然晚稻没法种了。”他皱着眉头说。于是我们又忙着挖沟排水,等把田里的水排得差不多了,天已经黑了。
傍晚收工,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家走,远远看见母亲还在菜地里择菜。她佝偻着背,动作缓慢而坚定。“妈,我来。”我跑过去,接过她手里的篮子。母亲的脸上满是汗水和泥土,眼睛却亮亮的:“不用,你歇着吧,回去把作业做了。”
“作业?”我苦笑着回应,“高考都考完了,还做什么作业?”
母亲愣了一下,似乎这才反应过来我已经是个高中毕业生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那就好好干活,别搞得最后不农不秀的。”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我又会被父亲叫醒。“快起来,趁凉快多干点活。”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母亲给我简单交代了做早餐、喂鸡鸭猪的任务,便搬起秧马,夹着捆秧草,踏着雄鸡打鸣声扯秧苗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从早到晚不停地劳作。抢收完了早稻,紧接着就是抢种晚稻。“晚稻一过秋,十有九不收”,大家都会赶在立秋之前把晚稻秧插满稻田。田里的泥土被太阳晒得发烫,赤脚踩上去,像踩在烧红的铁板上。插秧的时候,要长时间弯腰,我的腰疼得几乎直不起来,嘟哝着“腰痛死了”,这时候总会被“小孩子哪有腰”给怼回去。五代时期的高僧布袋和尚曾写过一首《插秧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诗意很美,但这时期水田里的蚂蟥是最疯狂的,即便母亲剪了一些旧衣袖给我们做防护套,但似乎无济于事。当我们收完工,饥肠辘辘地走出水田,脱了防护套,总会在腿肚、脚丫甚至胳膊上发现几条变得圆鼓鼓的饱腹蚂蟥。
双抢的日子里,时间似乎被拉长了,每一分钟都变得无比漫长;又似乎被压缩了,每一天都像打仗一样紧张。我们像一群不知疲倦的蚂蚁,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与天气赛跑,与时间赛跑。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个月。双抢终于熬到结束,家乡的田畴也从一片黄变成了一片青,我们都瘦了一圈,一身的痧皮和抓痕,晒得黢黑的皮肤正在褪皮,手指满是倒刺,脚丫也在溃烂,又痛又痒。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母亲将过年的最后一块腊肉煮了煮,切块炒了几个菜,配上咸得发齁的咸鸭蛋,父亲倒上没喝完的半瓶啤酒,边喝边说:“总算过去了。”经过双抢的轮训,入学体检我从120斤变成102斤,这也是我成年来最轻的体重。
劳累了一个暑假的大人,又开始打零工,或是帮邻居搭把手,或是去附近的工地干点小活儿,只为了多挣些钱,补贴家用,为孩子即将开始的求学之路储备资金。
与当下学子“高考后三件套”——考驾照、旅游、做头发不同,那时的“高考后三件套”是双抢、带娃、打零工。考完试的学生,不论中与不中,都要立即投入生活的洪流。有些学生或许能免于田间劳作,但带弟弟妹妹、帮衬家务却是免不了的。还有学生早已在考场外的小餐馆找好了暑期工的活计,一出考场,便系上围裙,开始了跑堂端盘子的营生。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带走了双抢的艰辛,也带来了生活的巨变。每年的这个时节,我在吹着空调的办公室看着远处的高楼大厦,总会恍惚觉得那些挥汗如雨的日子像是一场遥远的梦。但每当闻到稻穗的香气,记忆就会突然清晰起来——那些在烈日下弯腰劳作的身影,那些被汗水浸透的衣衫,那些咬牙坚持的日日夜夜,早已成为生命里最珍贵的勋章。现在的孩子们或许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对双抢有着如此复杂的情感。那不仅仅是一段艰苦的岁月,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无数普通人用双手创造生活的见证。双抢教会我们的,是在困境中坚持的勇气,是对土地的敬畏,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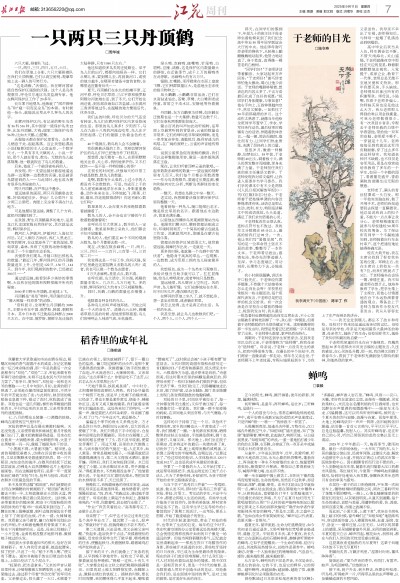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