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建
中秋将近,商超里各色月饼堆积如山。铁盒的、纸盒的,苏式的、广式的,豆沙的、蛋黄的,无奇不有。我每每走过,只略看一眼,它们包装华美,价格亦颇不菲,然而我知道,它们都不如我母亲做的五仁月饼。
我家的月饼,向来是母亲亲手做的。
每到中秋前两日,母亲便忙碌起来。她提前三天泡上糯米,加工成细腻的粉,再和上融化的猪油,和入温水白糖反复揉搓,揉成光润如玉的面团,摆在盆里,俨然一个白胖的娃娃。接着拌馅料,馅里含桃仁、花生米、赤豆、杏仁、瓜子仁。母亲把面团切成一小块,搓圆压扁,包入馅料,镶上芝麻,再搁进模子里压实。那模子是枣木的,用了许多年,边缘磨得发亮,已沁入了油香与甜气。母亲将模子反扣在案板上,轻轻一拍,一个月饼便脱了出来,上面印着“花好月圆”四字,周边还有缠枝的花纹。母亲做月饼时,眉眼低垂,嘴角微微上扬,仿佛手下不是月饼,而是什么极为贵重的物事。
月饼入炉烘烤,香气渐次溢出,先是面香,继而是五仁香,最后混为一体,成为一种独属于中秋的味道。
中秋节的晚上,父亲从堂屋里搬出八仙桌,放在院子中央。桌上摆上香炉、烛台,以及月饼、红菱、苹果等供品。小花狗跟在父亲脚边,跑进来跑出去,快活得直摇尾巴。我们则望着盘中的供品,垂涎欲滴。
夜幕降临,玉兔东升,皎洁的月光洒在地上像铺了层薄霜。父亲点亮红烛,燃了一炷香。神色庄重的他手持长香,面向刚刚出浴的月亮拜了几拜,再回过头将香插进香炉。我们瞪大眼睛,眺望天庭。今天的月亮,似崭新的玉盘,不染纤尘,清光四溢,格外清纯,格外皎洁。
父亲招招手,叫我们都去叩首拜月。我们学着父亲,一个接着一个跪倒在香炉前,虔诚地向月亮姑娘三磕头。父亲在旁喃喃祈祷:“嫦娥娘娘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保佑我家小孩学习好,长大有出息。”供桌上红烛摇曳,香烟袅袅,氤氲烟雾中,月亮亦真亦幻,笼罩了几分朦胧而又神秘的色彩。小花狗看着我们朝月亮跪拜,也向着天空“汪汪”地喊叫了几声。待我们都祭拜完毕,父亲吹灭蜡烛,撤去香炉烛台,方桌上,只留下月饼、花生等供品。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月饼,咬了一口。虽然是土月饼,却外皮酥脆,内馅甜糯,比姑妈买给奶奶的豆沙月饼还要好吃。
父亲搬了张藤椅,慢慢喝着茶。他不吃月饼,而是看月亮。月光洒在院墙边的桂花树上,落下满地碎金。“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圆!”父亲平时是个寡言的人,但每到中秋夜,他会指着月亮,给我讲许多关于月亮的故事,父亲上过私塾,在村里算是读书人。
“月亮是冷的。”他说,“上头有广寒宫,有桂树,有玉兔,有嫦娥——可是冷的,没有人气儿。”
我那时不解,只觉得月亮明晃晃的,如何会冷?父亲便解释:月亮自己不会发光,是借的太阳光。所以看着亮,实则没有热气。他说这话时,眼神邈远,仿佛不是在对我说,而是在对月亮说。
父亲又说,古人看月亮,看见的是乡愁,是离别,是相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月亮是乡愁;“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的月亮是祝愿。讲完了这些古诗词,父亲还给我们讲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等故事。
母亲的月饼、父亲的月亮,就这样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中秋。
后来我离家求学、工作,中秋往往不能回去。母亲便提前寄来月饼,依旧是五仁的,用油纸包着,裹了好几层。我收到时,月饼往往碎了些边角,但味道如旧。电话里,母亲总要问:“月饼收到了吗?没坏吧?”而父亲通常在旁边插一句:“今晚记得看月亮。”我咬了一口母亲做的月饼,五仁还是那样甜香,带着熟悉的味道。忽然明白,这么多年来,母亲的月饼里裹着的是家的味道,父亲望过的月亮里,藏着的是他对家人的牵挂。无论走多远,只要想起母亲的月饼,想起父亲陪我看月亮的夜晚,心里就总有一块地方是暖的——那是家的方向,是无论岁月怎么变,都不会消失的牵挂。
月光无声洒落,照着我,也照着千里之外的他们。天地间仿佛只剩下这一轮月,和无数颗被月光照得透亮的心。
母亲的月饼,父亲的月亮。一个甜而暖,一个亮而远。合在一起,便是中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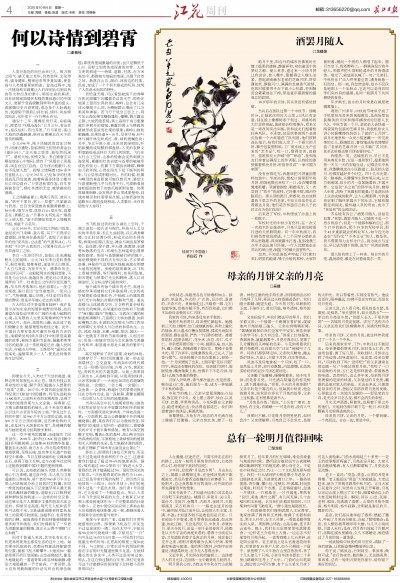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