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让眉
说起中国影响力最大的诗人,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不一定是王维。但若多几次追问,这名字出现的序位该也不会跑出前五。
王维常常出现在中国小朋友与诗的第一场邂逅里:孩子开蒙,少有不曾背过“红豆生南国”“空山不见人”的,不独如今,古时亦然。他的五言清逸流畅,兼具音乐性与画面感,是个舒适开放的美学端口——更难得还在成长性:王维的诗儿时读来可亲,大了观之忘俗,不学诗的觉它清新成诵,学过诗的对比过诸多仿作,则要益发敬畏它准确微妙。
能做到在每一种视觉焦距里都美很难。看过《格列佛游记》我们会意识到,巨人国里娇俏的女郎,在小人儿眼中不过是皮肤粗糙不堪、颜色不一的怪物——能做到入眼可爱,且每走近一步、每深入一层仍能美而不失度,其中必然包蕴着高于观察者理解层级的技艺。
科幻小说《三体》里有段情节,说三体文明派了一只被人类称为水滴的探测器来到太阳系,它小巧光滑,好像一滴水银。起初因为体积小,它并没有受到重视,但当科学家在一千万倍的、可以使大分子显像的显微镜下观察时,发现它的表面依然绝对光滑,才迅速产生了敬畏——后果也确实证明,在这个小而美丽的水滴面前,技术落后的地球舰队虽然庞大,但粗糙到不堪一击。看到这段剧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王维的诗:它正是与水滴一样的小巧、匀滑,拥有完美而看似毫无攻击性的弧度。
王维的诗也是用方块字组成的,同样遵循基本的格律,却没有近体诗特有的编织感。它很难被还原成一个个像素块,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用结构放缩的方法去拆解他的语言——王维拥有令大多诗人深羡的语言天才,但他诗的好处却不完全在语言这个维度。
古往今来,中国的好诗很多,但能同时禁得起不同角度审视的却很少。有的诗朗朗上口,但文辞粗陋;有的诗意象华丽,却佶屈聱牙;有的诗初见无味,要有阅历才能看出好处来;也有的诗乍看惊艳,却没有挖掘空间,禁不起成长后的回望。凝固的文本很难跟随读者变焦进行自我修正,而对大部分诗人来说,他们的魅力与缺陷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此之蜜糖,彼之砒霜,优势与劣势的消长从来不只在于诗人自己,读者的偏好也是重要的定义者。
但王维的诗却是个圆匀的弧形:他没有预留撒手锏,也相应失去了破绽——换言之,王维不是一位适合用现有诗学体系去定义个性的诗人,硬要去套的话,他可能在每个维度都刚好处于八十分的位置,均衡得令人提不起警惕,又仿佛是出于某种有针对性的设计。王维的诗从来不是我们情感上有紧急需求时可以即拿即用的工具,但同时,它又似乎总在不经意的余光里安然存在着。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想在这十五天里和你一起探索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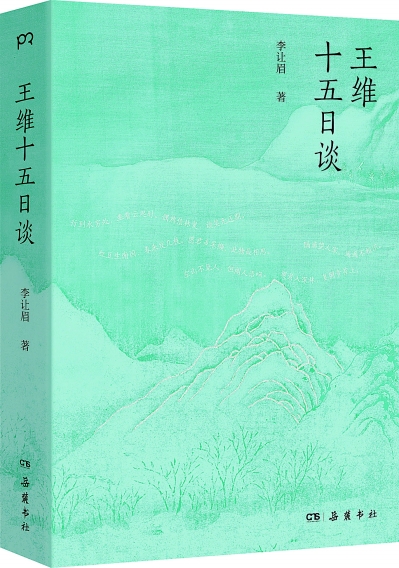
 朗读
朗读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